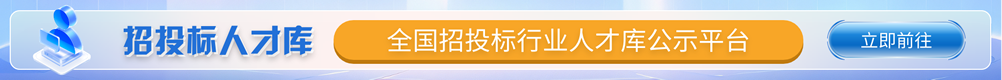全部選擇
反選
反選將當前選中的變為不選,未選的全部變為選中。

華北
華東
華中
華南
東北
西北
西南
其他
取消
確定
魯靖康|再論清代新疆“禁戲令”對戲曲活動的影響
所屬地區:新疆 - 烏魯木齊 發布日期:2025-09-08| 所屬地區: | 新疆 - 烏魯木齊 | 招標業主: | 略 登錄查看 | 信息類型: | 其他公告 |
| 更新時間: | 2025/09/08 | 招標代理: | 略 登錄查看 | 截止時間: | 略 登錄查看 |
咨詢該項目請撥打:15055702333
發布地址:(略)
來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3期
再論清代新疆“禁戲令”對戲曲活動的影響[1]
魯靖康
內容提要清政府在新疆曾三次限制和查禁戲曲。乾隆四十年的“限戲令”只針對駐防八旗,對戲曲發展影響有限。嘉慶十三年、道光十八年清廷又先后兩次在新疆發布“禁戲令”,迫使戲曲活動由公開轉入“隱秘”,(略)徑自由傳播和發展。除此之外,這兩次禁戲令造成的實際和具體影響此前可能被夸大了:戲班和戲曲改頭換面后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公開演出,(略)域還有擴大蔓延的趨勢,表演水平也未見衰頹。新疆建省后,禁戲令解除,清政府對待新疆戲曲活動的態度變化,反映出建省后新疆除行政制度與內地趨同外,文化政策也有了一體化的調整。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曾三次發布諭旨對新疆戲曲演出進行限制和禁止,學界對此卻少有關注,目前僅見有三位學者矚目于此:賈建飛探討乾隆至道光時期內地移民與新疆的戲曲發展情況,分析了嘉慶朝禁戲令對當地戲曲發展的影響。[2]彭秋溪在梳理乾嘉時期經濟開發與戲曲傳入的基礎上,對嘉慶、道光兩次查禁戲曲的原因和影響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探究,[3]方華玲亦對清代新疆查禁戲曲的原因和效果進行過簡要分析。[4]三位學者已經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探索,當前學界多認為清代新疆戲曲活動因禁令遭到嚴重打擊,陷入衰退,這個結論是否成立是關乎清代新疆戲曲發展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有必要辨明,因此本文擬重新對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一嘉慶十三年以前新(略)的戲曲活動
清代內地戲曲何時傳入新疆,史料當中并無明確的記載。據《新疆圖志》所述,乾隆年間清軍平定新疆時可能就有戲班跟隨大軍入疆:“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后。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供給于商。”[5]“聲色百伎之娛樂”應包括戲曲在內。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之后,內地人口陸續遷徙流寓而來,原為準噶爾游牧之地的北疆逐漸形成一些城鎮和聚落,漸趨繁華,其中尤以巴里坤、烏魯木齊最具代表性。內地移民到新疆后,將演戲的習俗也一并移植過來,營造出一種類似家鄉的文化氛圍。巴里坤“地方開辟日廣,人民漸增”“西成以后,兵民商賈無不感戴皇仁,報賽演劇,歌詠太平。”[6]烏魯木齊有滿漢兩城,(略),“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輻輳,茶寮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于關外”[7]。據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768~1771年)謫戍在此的紀昀記載,烏魯木齊有“酒樓數處,日日演劇,數錢賣座,略似京師”“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略)既罷,往往吹竹彈絲。”萬壽宮是慶賀皇帝生辰的處所,“遇圣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庫爾喀拉烏素亦同。”“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紀昀還提到烏魯木齊有“梨園”“歌童”數部,并列舉了幾位有名的戲曲演員:“梨園數部,遣戶中能昆曲者又自集為一部,以杭州程四為冠。”“歌童數部,初以佩玉、佩金一部為冠,近昌吉遣戶子弟新教一部,亦與相亞。”鱉羔子以生角擅場,簡大頭以丑角擅場,劉木匠以旦角擅場,遣戶何奇能以楚聲為艷曲等等。[8]
戲曲藝術發展到清代,已經成為城鄉居民不可或缺的娛樂形式。但在統治者看來,看戲聽曲會使人耽于享樂、荒廢本業;組織者為了展現財力、影響力,往往互相攀比,助長民間的奢靡之風;演出時人員大量聚集,有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必須加以限制,必要時甚至可以加以禁止。統一之初清政府聽任戲曲在新疆傳播發展,未加任何限制,隨著戲曲活動逐漸繁盛,如何將其納入可控范圍,成為清廷需要解決的一項議題。乾隆四十年(1775)新疆發生的幾起酒后斗毆致死案件引起了統治者的擔憂,為確保駐防八旗專務訓練,不受酗酒演劇等“敗壞風俗”習氣的影響,乾隆帝于該年九月發布諭令,對新疆戲曲活動進行限制:
諭軍機大臣等:伊犁、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等處設立駐防滿洲兵,特派將軍、大臣管理,原期不失滿洲本業,訓練講習,以成勁旅。該將軍大臣等,宜仰體朕心,實力整頓,方為無忝厥職。若戲園酒肆,最為敗壞風俗之端,尤宜嚴禁。乃近日新疆屢有因酒后斗毆斃命之案,皆由平日漫無約束所致。此事甚有關系,著傳諭該將軍、大臣等,嗣后務宜留心化導,隨時簡練,于聚飲演劇之事嚴行禁止,以副朕造就滿洲至意。倘視為具文,經朕察出,必將該將軍、大臣等治罪。[9]
接到諭旨后,有滿兵駐防的各地將軍、大臣陸續回奏,表態要嚴厲禁(略)內的滿兵飲酒唱戲。[10]乾隆這道諭旨和各地的回奏都僅針對新疆駐防滿洲兵,君臣本意均非要在新疆全面、徹底查禁戲曲。這一點在隨后發生的一些事關戲曲活動的案件處理上也能得到印證:禁令發布第二年,哈密就發生了唱戲民人高寶童將同戲班王敏戳傷致死的人命大案。高寶童原被問擬斬候,乾隆認為案發邊(略),須從嚴辦理,下令將兇手由次年秋審歸入當年秋審。[11]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私販玉石已被清廷下令“正法”的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又被查出在孝圣憲皇后(乾隆生母)守制期內“演戲聽曲”,乾隆下旨追加懲罰。[12]以上兩案,都與新疆戲曲活動有關,即便如此,乾隆對案件的處理也只是就案論案,除加重對涉案人員的處理外,并未殃及新疆的戲曲活動本身。筆者之所以特意強調乾隆禁戲令只是針對新疆駐防滿兵,而不是全面、徹底查禁,是因為它關涉到此后嘉慶發布全面禁戲令時對乾隆這道諭旨的解讀。
總之乾隆針對駐防滿兵的戲曲禁令就全疆范圍而言只能算是“限戲令”,對新疆戲曲發展影響有限。限令頒布之后,除前引哈密、葉爾羌兩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戲曲演出的記載。如乾隆五十年(1785)遣戍伊犁的趙鈞彤行至(略),見“近郭小村架秋千,方演劇,起高臺,男婦聚觀與內地等”[13]。五十四年,謫戍伊犁的王大樞與人合伙在惠遠城北郭開設“廉五酒坊”,開張之日“列筵演劇,披彩懸掛”[14]。
茲根據奏折檔案,將嘉慶十三年(1808)新疆全面查禁戲曲時,各地戲曲活動情況列表以示。
二嘉慶十三年新疆全面查禁戲曲及其影響
嘉慶十三年(1808),伊犁一戲班發生命案,唱戲民人王貴珍刺死了同班的龔明。[15]時任伊犁將軍松筠除將案件審結奏報外,又另折具奏,表達了對戲班活動的憂慮:“第恐年復一年,日漸加增,或致引誘農家子弟入班學戲,不但與地方風俗有礙,且恐將來年久,駐防子弟漸習下流。”折中提出三項應對之策:一是重申乾隆年間禁令,將乾隆四十年(1775)所頒諭旨通行各地駐扎大臣一體欽遵,繼續禁止駐防滿洲官兵飲酒唱戲。二是限制伊犁戲班數目,只許現有兩戲班活動,如有內地新來戲班,即行逐回。三是限制現有戲班規模,班中不許再添新人,若引誘農家子弟入班,查明治罪。[16]松筠的意見仍是像以前一樣加以限制,而非徹底查禁,只要戲班不影響駐防滿洲官兵,班數不再增加和吸納新人即可。嘉慶接報后卻認為松筠的意見“失之軟弱”,以有礙駐軍和地方風氣為由發布了全面禁戲令:
伊犁等處有官兵在彼駐扎,系屬軍營,自當專務訓練,俾知學習技勇,敦崇習尚,何得有演戲等事?從前乾隆四十年欽奉皇考高宗純皇帝諭旨:倘有開設酒肆唱戲等事,一經發覺,定將該將軍、大臣等一并治罪。可見禁約綦嚴,圣心早慮及于此。乃歷任將軍等奉行不力,致現在聚有戲班,是該將軍等已有應得之咎,猶不上緊驅逐,只議令嗣后不許添人。試思此時即不添人,而該處既有戲班,焉有農家子弟及駐防官兵不受其引誘之理?此于該處地方營伍大有關系,不可不力加整飭。著松筠即將該處戲班立行驅逐,速令自歸內地,不準在彼逗留。如尚敢潛留,即當治以違禁之罪。并通行南北各城一體凜遵,毋得縱容滋事。[17]
稍后又嚴申前令,措辭更加嚴厲:“(略),令該處駐扎大臣等一體凜遵,認真查察,凡有戲班人等俱著立時攆逐出境,令其各歸內地謀生,毋許逗留。仍將實力查禁緣由,于每歲年底自行具奏一次,無庸交伊犁將軍匯奏。設該大臣等陽奉陰違,飾詞具奏,將來經朕查出,必當治其欺罔之罪,不能寬恕。”[18]
對比嘉慶“禁戲令”和乾隆“限戲令”可以發現,嘉慶對乾隆限戲令所針對對象的理解上出現了偏差。在嘉慶看來,乾隆當年禁止的是新疆所有人的戲曲活動,不區分八旗、綠營、民人、商人,故而得知新疆還有戲班聚留后就嚴厲斥責各地奉行禁令不力。在皇權臻于鼎盛的清代,帝王意旨的正確性不容絲毫懷疑,對此松筠也只能解釋說當年伊勒圖接奉乾隆諭令“只以嚴禁駐防八旗,未免忽于雜處商民”[19]。正是嘉慶理解上的偏差,導致原本的“限戲令”意外升級為“禁戲令”。
松筠接到禁戲諭旨后,隨即飭令管理民事的撫民同知傳集鄉約,將戲班攆逐出境,又讓鄉約們出具甘結,保證不再有戲班及商民演劇之事。[20]然后行文南北各地駐扎大臣,要求一體驅逐戲班。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哈密、喀喇沙爾等有戲班(略)接到諭旨后迅速行動起來,將境內戲班驅逐出境,并將查禁結果相繼回奏。查明轄境沒有戲班的葉爾羌、烏什、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等地駐扎大臣也紛紛表示以后要實力查禁,防止戲班入境。[21]至嘉慶十三年底,新疆所屬十一個(略)全部將查禁戲班事務匯報完畢,[22]或查無戲班,或已驅逐凈盡。設有文官的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臺、哈密由當地文官具體負責查禁,不設文官的回疆“南八城”地區由駐扎的綠營官員具體負責查禁。[23]
需要說明的是,嘉慶禁戲令的對象主要是戲劇和曲藝,即俗稱的“看戲聽曲”,民間為慶祝豐收和節慶日舉行的社火、賽神等活動不在禁止之列。(略)后繼續活動埋下了伏筆。
按嘉慶要求,新疆各地駐扎大臣每年年底須將轄境查禁戲曲情況各自奏報一次,由此從嘉慶十三年開始,新疆各地年年奏(略)禁戲情形。從現存的此類奏折來看,其格式和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少有變化。都是先引嘉慶十三年上諭,然后說經過仔細查察,本年轄境內并無戲班,有些還附以將繼續嚴禁戲班、毫不懈怠之類的言辭。仿佛高壓之下,新疆戲班和戲曲活動真的銷聲匿跡了。如禁令頒布前戲曲活動最為活躍的烏魯木齊在嘉慶十五年(1810)奏報:“所有從前戲班俱經攆逐,散回內地,實無容留在境演唱之事。”“現在各屬地方一律肅清,兵民人等各務正業。”十六年又奏報:“內地戲班久知新疆查禁嚴密,亦無敢復行出口,各屬實無容留戲班私行演唱之事。”[24]“新疆無戲班”的結論看上去似乎不容懷疑,以致于學界推測“禁戲高壓之下,內地戲班似全部東歸”[25],或得出“原存新疆之各內地戲班只能盡行返回內地,新疆之戲曲業顯然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26]的結論。事實恐非如此。
嘉慶二十年(1815)十二月至二十四年(1819)三月,原江西(略)令史善長因罪發遣烏魯木齊,在此地生活了三年多的時間,賜還后寫有一部《輪臺雜記》。書中記載:烏魯木齊“民重賽會,自三月東岳會起,(略)鎮殆無虛日,至十月朔嚴寒乃罷”。“三月仙姑娘娘會最盛,廟在漢城北,搭臺演秧歌。”“次則城隍會、觀音會,”還有文昌會等等。所描述的賽會之盛絲毫不亞于紀昀所記,但沒有明確說該地演劇,唯一提到的“演秧歌”是否就是演戲尚需進一步考察。該書又云“口外例不演戲,年終匯奏,并咨軍機處。然商貨泉流,客民霧集,游手者不少。有秧歌部、女檔部,秧歌樂神,女檔娛賓。作升平之鼓吹,豢邊徼之窮黎,亦官法所不禁,采風所不廢也”[27]。“口外”是新疆的俗稱,“例不演戲”“年終匯奏”“咨軍機處”說的顯然是嘉慶十三年的禁戲令和各處須年終匯奏禁戲情況之事。“女檔娛賓”,女檔和女檔部自是娼妓和妓館的別稱。漢民有賽神時演戲的習俗,則樂神之秧歌和秧歌部指的應是唱戲者和戲班。再聯系到道光十八年(1838)成瑞所說“新疆禁止優戲,民間報賽,皆唱太平秧歌”[28],從而可以確定史善長所說的“演秧歌”和成瑞口中的“唱太平秧歌”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戲曲演出的諱稱。
《輪臺雜記》不但指出烏魯木齊留有戲班,而且還可以公開在廟會上演出。書中還記載了秧歌部戲女福兒被某大員豢養之事。[29]雍正、乾隆和嘉慶三朝曾多次發布諭令,禁止外官蓄養優伶和戲班,[30]而此大員竟置禁令于不顧。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句“亦官法所不禁”,朝廷明明有嚴厲的禁令,此處卻說官法不禁。而且史善長在烏魯木齊的三年期間,都統每年都向清廷奏報說該處沒有戲班容留。[31]
除烏魯木齊外,史善長的詩歌和歸程筆記當中還透露出烏魯木齊都統管轄的阜康以及濟木(略)妓館和酒肆茶坊又多是演戲之所。
道光十三年(1833),薩迎阿由烏什辦事大臣調任哈密辦事大臣,上任途經烏魯木齊時所作的詩中有“花欄粉黛開千戶,水磨亭臺起六家”的句子。“花欄”句下注:“漢城花巷有女如云”[34]。此花巷之女當中應有為數不少的優伶。經過吐魯番時,賦詩描繪當地“燈火攤錢(略),管弦呼酒上春臺”[35]。“春臺”即戲臺,“管弦”“春臺”二詞表明該地應該也有戲曲活動。吐魯番時為直隸廳,亦屬烏魯木齊都(略)。
嘉慶禁戲令發布之初的幾年里,新疆各地可能確實遵照禁令驅逐了戲班,由此導致暫時無戲班的局面。嘉慶十七年(1812)烏魯木齊領隊大臣恒杰在中秋節當天傳喚兵丁進署喝酒唱曲一案,[36]似能支撐這一推論:如有專業戲班,何至于傳喚兵丁?但從史善長的記載來看,這種無戲班的局面并未持續幾年,地方官對復來的戲班采取了默許態度,并未如實奏報和加以驅逐,戲曲活動也未受到嚴格限制,仍可以公開演出。
史善長將戲曲稱為“秧歌”,戲班稱為“秧歌部”,成瑞稱戲曲為“太平秧歌”。除此之外,也有將戲曲稱作“太平歌”的:道光十九年(1839),遣戍烏魯木齊的黃濬所作的詩中有“笙歌多在南梁上,且逐裙衫作浪游”的句子。自注曰:“南梁在迪化南門外,地多祠廟,太平歌叢集之所。”[37]可見禁令之下的戲曲演出并未絕跡,只是不再以唱戲相稱,而是改稱為“演秧歌”“唱太平秧歌”或“太平歌”。史善長所說的“秧歌”就是“太平秧歌”的簡稱,據此“太平秧歌”“太平歌”之類的稱呼早在嘉慶晚期就有,并非如有些學者所說遲至道光中葉才出現。[38]
總之嘉慶十三年的這次查禁戲曲并未達到預期效果,烏魯木齊的戲曲演出仍相當繁盛,甚至有大員違禁蓄養優伶,其所屬的阜康、濟木薩、吐魯番等地可能也有戲班和戲曲活動。
三道光十八年的禁戲令及光宣年間的戲曲政策
戲曲和戲班的改頭換面未能逃過清廷的耳目。道光十八年(1838),喀喇沙爾換防游擊伊林保控告此處辦事大臣海亮侵蝕公項,私役兵丁署內唱戲、傳喚倡優等罪名。[39]清廷在命人查辦此案的過程當中發布了第二道禁戲令:
諭軍機大臣等:(略)為邊防要地,該處將軍、大臣等固當廉明表率,即員弁、兵丁亦應操防練習,屏斥嬉游,方為有備無患。朕聞該處近多演劇游戲,以唱太平歌為名,彩服登場,歡呼取樂,竟有兵丁扮作戲劇,蕩檢逾閑,不成事體。兵弁習勤講武,日久自成勁旅,似此違例玩法,尚安望其折沖御侮耶?著奕山、廉敬、恩特亨額等細加訪察,如有此種惡習,立即嚴行懲辦,毋使相沿日久,漸染澆風,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40]
這道禁戲令說明此前嘉慶禁戲的效果并不理想:新疆仍有戲曲活動,(略),而且還有駐軍參與演戲的行為。此諭有兩層意思,一是繼續禁止以唱太平歌為名的演劇活動,二是尤其要禁止兵丁演戲,包括滿洲兵也包括綠營兵。諭旨中點名的奕山時任統轄全疆的伊犁將軍,廉敬任管轄北疆(略)的烏魯木齊都統,恩特亨額任總理南八城事務的葉爾羌參贊大臣。道光本意是要通過他們傳達給各自所轄的駐扎大臣(略),進而覆蓋全疆,但從結果來看,這道諭令只傳到了奕山駐扎的伊犁和恩特亨額駐扎的葉爾羌兩處,未能覆蓋兩大臣所轄的(略)域,而且連諭旨當中點名的廉敬任都統的烏魯木齊都沒有傳達到,遑論其所(略)。
自該年起新疆各地奏報的禁戲折有了一些內容(略)別:接到道光禁戲諭令的伊犁和葉爾羌在奏報時先引嘉慶十三年禁戲諭旨,再引道光十八年禁戲令。因為需要稽查兵丁,所以兩處負責稽查的官員也有變化:伊犁負責查禁的官員除管理民事的撫民同知外,還加入了管理滿營的領隊大臣、協領以及管理綠營的總兵。[41]葉爾羌也相應對稽查官員作了調整,綠營參將繼續負責稽查地方有無戲班,另委印房章京訪察有無兵丁扮作戲劇情事。[42]而烏魯木齊和其他各地因沒有收到道光十八年的禁令,奏報仍然沿襲嘉慶十三年禁戲折的格式和基本內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大量新疆各地駐扎大臣奏報的禁戲折,最早是嘉慶十三年,最晚延至同治二年(1863)。[43]奏報的形式有專折具奏,也有另片附奏。奏報時間一般在當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也有個別提前至十月底或延至次年正月。皇帝的批示絕大多數只是“覽”或“知道了”寥寥數字,極少數有一些勉勵的話語,如“仍應認真稽查,毋稍疏懈”[44]。道光十八年以后各地奏報的結果仍是每年本境并無戲班,伊犁、葉爾羌還附加奏報說沒有兵丁唱戲。但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仍先以烏魯木齊為例,前引成瑞、黃濬的詩作及詩注已經說明道光禁戲當年和次年,該地仍有戲曲演出活動。此外黃濬遣戍烏魯木齊期間(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六年)所作的《紅山碎葉》對此處戲曲有更為細致的記載:當地有大鳳班、小鳳班、江東班等數個戲班,其中大鳳班還是某鳳姓旗員所蓄。并說:“口外諱言‘戲’,以有厲禁,謂之‘太平歌’。”“俗以六月六日大會于紅山嘴之火神廟,臺閣戲劇,鉦鼓喧闐,士女云集。”當地官吏每年在城外智珠山舉行“案牘會”,“演戲于山下沙磧上。”“正(略)最盛,例禁演戲,避其名謂之‘太平歌’。”[45]
刊于咸豐元年(1851)、反映道光時期之事的唱詞《出口外歌》中說“出口人”到烏魯木齊后,經常“到午間往大街去把戲看”,而且結識的當地妓女也提到常常看戲。[46]咸豐元年倭仁出任葉爾羌幫辦大臣,行至吐魯番勝金臺時看到“村墟演劇酬神”[47]。咸豐二年遣戍烏魯木齊的楊炳堃走到木壘,“適屆會,市演劇酬神,信步至會,周游一過,”[48]留有“煙火千(略)廛,踏歌聲里奏神弦”[49]的詩句。吐魯番和木壘同屬烏魯木齊都統管轄。
再看伊犁的情況。林則徐曾因禁煙而遣戍伊犁惠遠城,日記當中多次記載該地的戲曲活動。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元宵節“市上有演臺閣、唱秧歌者”,“唱秧歌”即唱戲的諱稱。二月十二日,惠遠城西關外“見鄉間演劇,觀者如堵”。十五日,北關外“見大神廟中演劇”。十九日攜兩兒“同赴大士廟觀劇”[50]。
南疆喀喇沙爾和葉爾羌也有戲曲演出。道光二十五年林則徐赴南疆勘荒,六月十九日見喀喇沙爾西門外“以觀音佛誕演劇,觀者如堵”[51]。咸豐十一年(1861),葉爾羌參贊大臣英蘊因母親過壽,將舊有太平社藝人叫至私舍演戲。[52]此“太平社”應得名于“太平歌”,亦是戲班。
黃濬曾批評烏魯木齊的戲曲表演“曲目鄙俗、情節支離,裝男腳色則跳舞為能,裝女腳色則面目可丑,直不可以言‘戲’”[53]。有學者據此認為:禁令之下“當地應該并沒有內地那樣非常正規和專業的戲班存在,此類所謂之戲或許只是當地民人一種較為原始粗俗的娛樂形式。”或因此推論“‘太平歌’與乾嘉時期當地戲班的規模、戲曲表演形式已很大不同,已偏向于‘舞蹈’表演”[54]。筆者認為黃濬的評價出自個人喜好,并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結論。黃濬乃浙江臺州人,出仕后又一直在江西為官,兩省都流行曲詞典雅、行腔婉轉、表演細膩的昆曲,與新疆流行的曲子戲在曲目名稱:(略)
筆者也不贊同“鑒于禁戲的余威,戲班的主要活動轉至城外關(略)”和“因(略)禁戲的嚴格,一些戲班似乎(略)轉移至村落”[55]的觀點。前一說法引用黃濬“南梁在迪化南門外,地多祠廟,太平歌叢集之所”之語來論證。祠廟前唱戲是為酬神,只要空間條件允許,唱戲自然要在祠廟前進行,南梁既多祠廟就定是太平歌叢集的地方,這跟禁不禁戲無關。而且古(略)內部空間一般比較狹隘,只會建設少數重要的壇廟,多數祠廟會建于城外。后一說法引用倭仁在吐魯番勝金臺見到的“村墟演劇酬神”來證明,勝金臺是吐魯番境內的一處軍臺,確是屬于村落等級的居民點,但村落唱戲未必是因為城鎮禁唱。戲班是賣藝謀生,何處請邀去何處,到村落唱戲與城鎮禁唱沒有必然關聯。
以上幾種觀點都是在所掌握史料缺乏反證的情況下,基于禁戲令的存在和奏折“無戲班”的結論作出的推測,夸大了禁戲令的影響。事實上此次禁戲的覆蓋面和力度遠不及嘉慶十三年那次,效果也不如之。不但烏魯木齊及其所(略)戲曲繼續存在和公開演出,而且伊犁、喀喇沙爾、葉爾羌等地也出現了戲班和戲曲活動的記載,表明新疆戲曲非但沒有禁絕,反而得到進一步蔓延發展,并且仍有官員違禁蓄養戲班。
清廷最后一次重申新疆禁止演戲是同治即位之初。[56]同治三年(1864)起新疆陷入十余年的戰亂之中,受兵燹影響,未見戲曲活動的記錄。光緒初年清軍收復新疆,隨著社會環境趨于安定,戲曲活動逐漸再次勃興。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建省后清廷全面禁止該地演戲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解除,而不是目前學界所說的“削弱”或“松弛”[57]。
光緒十六年(1890),古城城守尉德勝控告鎮迪道道員恩綸在忌辰之期演戲宴客。陜甘總督楊昌濬調查后匯報,恩綸并未在忌辰之日演戲宴客,并說:“新疆雖遠處關外,凡遇忌辰齋戒從不演戲,至今例禁綦嚴。”[58]宣統二年(1910),御史瑞賢參劾新疆布政使王樹枏于光緒“國服未闕”之期,藉母壽張筵演劇等罪名。陜甘總督長庚派人調查后回奏:王樹枏為母祝壽唱戲屬實,但一接到光緒駕崩的電文就立即停止,建議此項罪名“應免其置議”[59]。后王樹枏雖被開缺調京,但并非演戲所致。[60]兩份奏折不但直言新疆存有戲班,而且被控告的兩人一因未在忌辰演戲、一因聽聞皇帝駕崩即停止演戲而免于懲處,表明清廷的全面禁戲令已經解除,新疆只需與其他省份一樣遵守忌辰齋戒之日不演戲的規定即可。
以上是官方組織的演戲案例,再來看民間的戲曲活動情況。1902年德國人卡恩·德雷爾(CarenDreyer)“考察”吐魯番,行至烏蘇時記載:“當我們進城的時候,窄(略)場上正在唱戲,真是一道色彩絢麗的美景!”還說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途中的客棧有時候會滿員,“因為商人、中國官員或者走村串巷的戲子們都會住在這里。”[61]表明戲曲活動在民間也較為普遍。
有觀點認為道光十八年以后至清朝滅亡,新疆一直全面禁戲,故而將湘軍收復新疆以后的這段時間合并討論,在列舉了烏魯木齊太平歌、勝金臺演劇酬神以及咸豐至宣統期間的數則戲曲演出案例之后,得出本階段戲曲“較之乾隆后期至嘉慶前期,顯然大為衰頹”的結論,并認為“這種種情形,自然不能歸為載記的缺失,而應歸因于西(略)驅逐戲班東歸內地這一事實”[62]。前文已經論證,道光十八年至同治戰亂前,新疆戲曲仍在繼續發展,光宣時期禁戲令解除,新疆戲曲因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今天的新疆戲曲事業正是植根于這個時期。[63]說其大為衰頹恐與史實不合,因缺乏史料而再次夸大了禁戲令的影響。
四結語
清軍入關后統治者為了保持本族文化、維持軍事優勢,對本族接觸漢文化多有限制。就戲曲領域而言,清帝曾多次發布諭令,限制或禁止旗人聽戲、唱戲。這些禁令并非只針對新疆,京師對戲曲的管控更嚴,京師之外的陪都盛京以及西藏也有限制戲曲活動的諭令,只是不似京師和新疆這般嚴格。無論是乾隆限戲令,還是嘉道禁戲令,都以防止駐軍腐化、維持戰斗力為出發點,反映出統治者對西北軍政和邊防的重視。統治者對可能影響軍隊紀律、習氣和戰斗力的行為加以限制或禁止,本無可厚非,但如何在達到目的的前提下避免擴大化而“傷及無辜”,體現的則是統治者的眼界和智慧。流入新疆的內地民眾只有通過移植、復制包括戲曲在內的故鄉文化記憶才能對新環境產生認同和依賴,進而“各安生業”,維持邊疆穩定。乾隆能認識到戲曲等傳統文化對于新疆內地移民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意義,故能(略)別地加以對待,而繼任的嘉慶、道光卻只知變本加厲地嚴禁和取締,從而造成朝廷法令與民眾習俗的嚴重沖突。
必須承認,嘉道兩次禁戲令的發布對新疆戲曲活動的影響是顯著的,它迫使戲曲活動由公開轉入“隱秘”,(略)活動,(略)徑自由傳播和發展。在這個前提下重新審視禁戲令的實際、具體效果,其對新疆戲曲發展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此前可能被夸大了。從兩次全面禁戲后新疆的戲曲演出情況來看,禁令除了頒布之初的短時間內可能有效外,總體上并未達到預期目的,戲曲和戲班改頭換面后繼續公開活動,且有擴大蔓延的趨勢,還有官員違禁唱戲,甚至蓄養優伶,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新疆的戲曲表演水平發生了衰頹。
考察清代新疆的戲曲活動必須(略)域差異。哈密、吐魯番因地處要沖,流寓和行經的內地人口較多,南八(略)的戲曲活動遠沒有內地人口聚集的北疆,尤其是烏魯木齊及其所(略)發達。考察禁戲令的影響時也應考慮這一差異,南八城某些偏遠的地方,如和(略)可能確實長期沒有戲曲活動,禁與不禁差別不大;但北疆不同,禁令前后戲曲活動的變化更能體現出查禁的效果和影響,因此更具有樣本意義和說服力。這樣的典型樣本首推烏魯木齊及其所(略),次則巴里坤、伊犁。
盡管本文補充了不少禁戲令下戲曲演出的資料,但展示的仍然不是清代新疆戲曲活動的全部面相。因為禁令的長期存在,我們無法從官方口徑獲得更多有價值的信息,只能主要依賴游歷、為官或遣戍新疆者的私人筆記、日記、詩歌等材料。城鎮人口集中,賽神演劇較多,還有專門的酒肆戲園,而其他較為偏僻的地方一般逢節慶才會演出戲曲,不一定被西行東歸者遇到,況且戲曲演出在內地很常見,即使遇到也不一定會記載下來,所以實際上的戲曲演出活動應該比本文列舉的還要多,這就更進一步說明禁戲令的不理想。真正對清代新疆戲曲活動造成致命打擊的并非禁戲令,而是同光年間的戰亂。晚清新疆禁戲令解除,新疆戲曲活動由此進入了自由發展階段,今日新疆的戲曲事業正是奠基于此。從建省前后清政府對待新疆戲曲活動的態度變化,可以看出新疆建省后除行政制度與內地趨同之外,文化政策也有了一體化的調整。
滑動查閱注釋
[1]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州縣建置視角的清代新疆治理研究”((略):20BZS146)階段性成果。刊出時吸收了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與《西域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2025年西北邊疆研究工作坊:清代新疆的‘治’與‘安’”會議上專家提出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了修改,在此表示感謝。
[2]賈建飛:《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85~194頁;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5~31頁。
[3]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63~279頁。
[4]方華玲:《論清代的禁戲制度》,《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4期,第39~41頁。
[5]〔清〕王樹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77頁。
[6]《奏聞巴里坤城迤西四十余里之花莊一帶開水渠增墾荒地情形》,乾隆三十年十月十七日陜甘總督楊應琚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朱批奏折,檔號:“故宮”047389。
[7]〔清〕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卷一《新疆紀略上》,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清刻本,第6頁。
[8]〔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載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2~187頁。
[9]《清高宗實錄》卷九九一,乾隆四十年九月癸酉。
[10]《奏遵旨查禁伊犁駐防滿洲兵丁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初一日伊犁將軍伊勒圖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25;《奏遵旨禁止塔爾巴哈臺八旗官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初八日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慶桂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11;《奏遵旨禁止葉爾羌駐防滿洲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二日葉爾羌辦事大臣瑪興阿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38;《奏遵旨嚴禁烏什滿洲官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烏什參贊大臣綽克托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33。這只是現存奏折,應還有一些奏折沒能保存下來。
[11]《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一,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寅。
[12]《清高宗實錄》卷一○六九,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乙亥。
[13]〔清〕趙鈞彤:《西行日記》,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略),1996年,第155頁。
[14]〔清〕王大樞:《西征錄》卷四《廉五酒坊》,國家圖書館館藏民國抄本,(略):地800/8547,無頁碼。王大樞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抵達伊犁戍所(見同書卷二),開設酒坊的時間為“予來伊犁之二年”,即到戍后第二年。
[15]《奏為綏定城民王貴珍扎斃同班龔明擬絞監候事》,嘉慶十三年三月初五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16]《奏為遵旨駐防官兵查禁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三月初五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17]《清仁宗實錄》卷九四,嘉慶十三年四月丁卯。
[18]《奏為遵旨通飭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六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此處所引嘉慶諭旨為該折抄引,諭旨發布時間為嘉慶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19]《奏為遵旨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五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20]《奏為遵旨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五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21]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0~273頁。作者所引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多數也有收藏,限于文章篇幅,各地驅逐戲班詳情不再摘引奏折一一敘述,具體內容可參閱此文。
[22]十一個(略)是伊犁、塔爾巴哈臺、烏魯木齊(兼轄巴里坤、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等地)、哈密、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
[23]“南八城”指地處天山以南的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屬喀什噶爾)、和闐等八城及其所(略)。
[24]《奏為查明新疆各屬地方并無戲班演唱事》,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6-006。《奏為遵旨烏魯木齊并無戲班演戲事》,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5-047。
[25]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4頁。
[26]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頁。
[27]〔清〕史善長:《輪臺雜記·上》,載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61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508~510頁。
[28]〔清〕成瑞:《輪臺雜詠》,見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7頁。
[29]〔清〕史善長:《輪臺雜記·上》,載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62冊),第72頁。
[30]〔清〕托津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九《吏部·處分例·居官燕游》,嘉慶二十三年內府刊本,第15~17頁。
[31]《奏為遵查新疆地方本年并無容留戲班演戲事》,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高杞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3-024;《奏為嘉慶二十二年份新疆地方并無容留戲班演唱情形事》,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烏魯木齊都統慶祥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1-012;《奏為遵旨新疆地方查禁戲班事》,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慶祥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7-015。
[32]〔清〕史善長:《至阜康》,編寫組:《歷代西域詩選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8頁。
[33]〔清〕史善長:《東還紀略》,清光緒刻本,第3頁。
[34]〔清〕薩迎阿:《烏魯木齊》,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47~348頁。
[35]〔清〕薩迎阿:《土魯番》,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47頁。
[36]《奏為遵旨審明烏魯木齊領隊恒杰與兵丁飲酒彈唱并私用馱價剩銀一案按律定擬事》,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9-045。
[37]〔清〕黃濬:《中元后二日曉霽》,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78頁。
[38]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5頁。
[39]《奏為喀喇沙爾換防游擊伊林保稟揭該城辦事大臣海亮等各劣款請派欽差大臣查辦事》,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40]《清宣宗實錄》卷三一三,道光十八年八月庚辰。
[41]《奏為伊(略):(略)。
[42]《奏為查明葉爾羌境內并無戲班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43]《奏報新疆地方并無容留戲班及演戲之事》,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伊犁將軍常清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錄副奏折,編號:“故機”095454。
[44]《奏為境內查禁戲班事》,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庫車辦事大臣承芳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5-015。
[45]〔清〕黃濬:《紅山碎葉》,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民俗文獻》第118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103~104、107、111~112、126頁。
[46]張貴喜,張偉編著:《山陜古逸民歌俗調錄》,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55~56頁。
[47]〔清〕倭仁:《莎車行紀》,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第497頁。
[48]〔清〕楊炳堃:《西行記程》,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第454頁。
[49]〔清〕楊炳堃:《過木壘河》,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94頁。
[50]周軒,劉長明編注:《林則徐新疆資料全編》,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88~291頁。
[51]周軒,劉長明編注:《林則徐新疆資料全編》,第336頁。
[52]《清穆宗實錄》卷一○,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丙申。
[53]〔清〕黃濬:《紅山碎葉》,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民俗文獻》第118冊,第104頁。
[54]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頁;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6頁。
[55]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6、277頁。
[56]《清穆宗實錄》卷二,咸豐十一年八月己未。此時咸豐已逝,(略)。
[57]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8頁;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頁。
[58]《奏為查明甘肅鎮迪道恩綸被參各節事》,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六日陜甘總督楊昌濬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7-094。
[59]《奏為遵旨查明新疆布政使王樹枬被參各節復陳事》,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陜甘總督長庚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0-126。
[60]《宣統政紀》卷五四,宣統三年五月己亥。
[61]〔德〕卡恩·德雷爾著;陳婷婷譯:《絲路探險:1902—1914年德國考察隊吐魯番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0、36頁。
[62]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31頁;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5~278頁。
[63]徐玉梅主編:《新疆曲子》,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新疆電子音像出版社,2015年,第1~45頁。
(作者單位:(略)
編校:楊春紅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霞
掃碼關注我們微信:(略)
郵箱:(略)
來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3期
再論清代新疆“禁戲令”對戲曲活動的影響[1]
魯靖康
內容提要清政府在新疆曾三次限制和查禁戲曲。乾隆四十年的“限戲令”只針對駐防八旗,對戲曲發展影響有限。嘉慶十三年、道光十八年清廷又先后兩次在新疆發布“禁戲令”,迫使戲曲活動由公開轉入“隱秘”,(略)徑自由傳播和發展。除此之外,這兩次禁戲令造成的實際和具體影響此前可能被夸大了:戲班和戲曲改頭換面后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公開演出,(略)域還有擴大蔓延的趨勢,表演水平也未見衰頹。新疆建省后,禁戲令解除,清政府對待新疆戲曲活動的態度變化,反映出建省后新疆除行政制度與內地趨同外,文化政策也有了一體化的調整。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曾三次發布諭旨對新疆戲曲演出進行限制和禁止,學界對此卻少有關注,目前僅見有三位學者矚目于此:賈建飛探討乾隆至道光時期內地移民與新疆的戲曲發展情況,分析了嘉慶朝禁戲令對當地戲曲發展的影響。[2]彭秋溪在梳理乾嘉時期經濟開發與戲曲傳入的基礎上,對嘉慶、道光兩次查禁戲曲的原因和影響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探究,[3]方華玲亦對清代新疆查禁戲曲的原因和效果進行過簡要分析。[4]三位學者已經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探索,當前學界多認為清代新疆戲曲活動因禁令遭到嚴重打擊,陷入衰退,這個結論是否成立是關乎清代新疆戲曲發展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有必要辨明,因此本文擬重新對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一嘉慶十三年以前新(略)的戲曲活動
清代內地戲曲何時傳入新疆,史料當中并無明確的記載。據《新疆圖志》所述,乾隆年間清軍平定新疆時可能就有戲班跟隨大軍入疆:“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后。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供給于商。”[5]“聲色百伎之娛樂”應包括戲曲在內。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之后,內地人口陸續遷徙流寓而來,原為準噶爾游牧之地的北疆逐漸形成一些城鎮和聚落,漸趨繁華,其中尤以巴里坤、烏魯木齊最具代表性。內地移民到新疆后,將演戲的習俗也一并移植過來,營造出一種類似家鄉的文化氛圍。巴里坤“地方開辟日廣,人民漸增”“西成以后,兵民商賈無不感戴皇仁,報賽演劇,歌詠太平。”[6]烏魯木齊有滿漢兩城,(略),“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輻輳,茶寮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于關外”[7]。據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768~1771年)謫戍在此的紀昀記載,烏魯木齊有“酒樓數處,日日演劇,數錢賣座,略似京師”“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略)既罷,往往吹竹彈絲。”萬壽宮是慶賀皇帝生辰的處所,“遇圣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庫爾喀拉烏素亦同。”“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紀昀還提到烏魯木齊有“梨園”“歌童”數部,并列舉了幾位有名的戲曲演員:“梨園數部,遣戶中能昆曲者又自集為一部,以杭州程四為冠。”“歌童數部,初以佩玉、佩金一部為冠,近昌吉遣戶子弟新教一部,亦與相亞。”鱉羔子以生角擅場,簡大頭以丑角擅場,劉木匠以旦角擅場,遣戶何奇能以楚聲為艷曲等等。[8]
戲曲藝術發展到清代,已經成為城鄉居民不可或缺的娛樂形式。但在統治者看來,看戲聽曲會使人耽于享樂、荒廢本業;組織者為了展現財力、影響力,往往互相攀比,助長民間的奢靡之風;演出時人員大量聚集,有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必須加以限制,必要時甚至可以加以禁止。統一之初清政府聽任戲曲在新疆傳播發展,未加任何限制,隨著戲曲活動逐漸繁盛,如何將其納入可控范圍,成為清廷需要解決的一項議題。乾隆四十年(1775)新疆發生的幾起酒后斗毆致死案件引起了統治者的擔憂,為確保駐防八旗專務訓練,不受酗酒演劇等“敗壞風俗”習氣的影響,乾隆帝于該年九月發布諭令,對新疆戲曲活動進行限制:
諭軍機大臣等:伊犁、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等處設立駐防滿洲兵,特派將軍、大臣管理,原期不失滿洲本業,訓練講習,以成勁旅。該將軍大臣等,宜仰體朕心,實力整頓,方為無忝厥職。若戲園酒肆,最為敗壞風俗之端,尤宜嚴禁。乃近日新疆屢有因酒后斗毆斃命之案,皆由平日漫無約束所致。此事甚有關系,著傳諭該將軍、大臣等,嗣后務宜留心化導,隨時簡練,于聚飲演劇之事嚴行禁止,以副朕造就滿洲至意。倘視為具文,經朕察出,必將該將軍、大臣等治罪。[9]
接到諭旨后,有滿兵駐防的各地將軍、大臣陸續回奏,表態要嚴厲禁(略)內的滿兵飲酒唱戲。[10]乾隆這道諭旨和各地的回奏都僅針對新疆駐防滿洲兵,君臣本意均非要在新疆全面、徹底查禁戲曲。這一點在隨后發生的一些事關戲曲活動的案件處理上也能得到印證:禁令發布第二年,哈密就發生了唱戲民人高寶童將同戲班王敏戳傷致死的人命大案。高寶童原被問擬斬候,乾隆認為案發邊(略),須從嚴辦理,下令將兇手由次年秋審歸入當年秋審。[11]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私販玉石已被清廷下令“正法”的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又被查出在孝圣憲皇后(乾隆生母)守制期內“演戲聽曲”,乾隆下旨追加懲罰。[12]以上兩案,都與新疆戲曲活動有關,即便如此,乾隆對案件的處理也只是就案論案,除加重對涉案人員的處理外,并未殃及新疆的戲曲活動本身。筆者之所以特意強調乾隆禁戲令只是針對新疆駐防滿兵,而不是全面、徹底查禁,是因為它關涉到此后嘉慶發布全面禁戲令時對乾隆這道諭旨的解讀。
總之乾隆針對駐防滿兵的戲曲禁令就全疆范圍而言只能算是“限戲令”,對新疆戲曲發展影響有限。限令頒布之后,除前引哈密、葉爾羌兩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戲曲演出的記載。如乾隆五十年(1785)遣戍伊犁的趙鈞彤行至(略),見“近郭小村架秋千,方演劇,起高臺,男婦聚觀與內地等”[13]。五十四年,謫戍伊犁的王大樞與人合伙在惠遠城北郭開設“廉五酒坊”,開張之日“列筵演劇,披彩懸掛”[14]。
茲根據奏折檔案,將嘉慶十三年(1808)新疆全面查禁戲曲時,各地戲曲活動情況列表以示。
二嘉慶十三年新疆全面查禁戲曲及其影響
嘉慶十三年(1808),伊犁一戲班發生命案,唱戲民人王貴珍刺死了同班的龔明。[15]時任伊犁將軍松筠除將案件審結奏報外,又另折具奏,表達了對戲班活動的憂慮:“第恐年復一年,日漸加增,或致引誘農家子弟入班學戲,不但與地方風俗有礙,且恐將來年久,駐防子弟漸習下流。”折中提出三項應對之策:一是重申乾隆年間禁令,將乾隆四十年(1775)所頒諭旨通行各地駐扎大臣一體欽遵,繼續禁止駐防滿洲官兵飲酒唱戲。二是限制伊犁戲班數目,只許現有兩戲班活動,如有內地新來戲班,即行逐回。三是限制現有戲班規模,班中不許再添新人,若引誘農家子弟入班,查明治罪。[16]松筠的意見仍是像以前一樣加以限制,而非徹底查禁,只要戲班不影響駐防滿洲官兵,班數不再增加和吸納新人即可。嘉慶接報后卻認為松筠的意見“失之軟弱”,以有礙駐軍和地方風氣為由發布了全面禁戲令:
伊犁等處有官兵在彼駐扎,系屬軍營,自當專務訓練,俾知學習技勇,敦崇習尚,何得有演戲等事?從前乾隆四十年欽奉皇考高宗純皇帝諭旨:倘有開設酒肆唱戲等事,一經發覺,定將該將軍、大臣等一并治罪。可見禁約綦嚴,圣心早慮及于此。乃歷任將軍等奉行不力,致現在聚有戲班,是該將軍等已有應得之咎,猶不上緊驅逐,只議令嗣后不許添人。試思此時即不添人,而該處既有戲班,焉有農家子弟及駐防官兵不受其引誘之理?此于該處地方營伍大有關系,不可不力加整飭。著松筠即將該處戲班立行驅逐,速令自歸內地,不準在彼逗留。如尚敢潛留,即當治以違禁之罪。并通行南北各城一體凜遵,毋得縱容滋事。[17]
稍后又嚴申前令,措辭更加嚴厲:“(略),令該處駐扎大臣等一體凜遵,認真查察,凡有戲班人等俱著立時攆逐出境,令其各歸內地謀生,毋許逗留。仍將實力查禁緣由,于每歲年底自行具奏一次,無庸交伊犁將軍匯奏。設該大臣等陽奉陰違,飾詞具奏,將來經朕查出,必當治其欺罔之罪,不能寬恕。”[18]
對比嘉慶“禁戲令”和乾隆“限戲令”可以發現,嘉慶對乾隆限戲令所針對對象的理解上出現了偏差。在嘉慶看來,乾隆當年禁止的是新疆所有人的戲曲活動,不區分八旗、綠營、民人、商人,故而得知新疆還有戲班聚留后就嚴厲斥責各地奉行禁令不力。在皇權臻于鼎盛的清代,帝王意旨的正確性不容絲毫懷疑,對此松筠也只能解釋說當年伊勒圖接奉乾隆諭令“只以嚴禁駐防八旗,未免忽于雜處商民”[19]。正是嘉慶理解上的偏差,導致原本的“限戲令”意外升級為“禁戲令”。
松筠接到禁戲諭旨后,隨即飭令管理民事的撫民同知傳集鄉約,將戲班攆逐出境,又讓鄉約們出具甘結,保證不再有戲班及商民演劇之事。[20]然后行文南北各地駐扎大臣,要求一體驅逐戲班。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哈密、喀喇沙爾等有戲班(略)接到諭旨后迅速行動起來,將境內戲班驅逐出境,并將查禁結果相繼回奏。查明轄境沒有戲班的葉爾羌、烏什、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等地駐扎大臣也紛紛表示以后要實力查禁,防止戲班入境。[21]至嘉慶十三年底,新疆所屬十一個(略)全部將查禁戲班事務匯報完畢,[22]或查無戲班,或已驅逐凈盡。設有文官的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臺、哈密由當地文官具體負責查禁,不設文官的回疆“南八城”地區由駐扎的綠營官員具體負責查禁。[23]
需要說明的是,嘉慶禁戲令的對象主要是戲劇和曲藝,即俗稱的“看戲聽曲”,民間為慶祝豐收和節慶日舉行的社火、賽神等活動不在禁止之列。(略)后繼續活動埋下了伏筆。
按嘉慶要求,新疆各地駐扎大臣每年年底須將轄境查禁戲曲情況各自奏報一次,由此從嘉慶十三年開始,新疆各地年年奏(略)禁戲情形。從現存的此類奏折來看,其格式和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少有變化。都是先引嘉慶十三年上諭,然后說經過仔細查察,本年轄境內并無戲班,有些還附以將繼續嚴禁戲班、毫不懈怠之類的言辭。仿佛高壓之下,新疆戲班和戲曲活動真的銷聲匿跡了。如禁令頒布前戲曲活動最為活躍的烏魯木齊在嘉慶十五年(1810)奏報:“所有從前戲班俱經攆逐,散回內地,實無容留在境演唱之事。”“現在各屬地方一律肅清,兵民人等各務正業。”十六年又奏報:“內地戲班久知新疆查禁嚴密,亦無敢復行出口,各屬實無容留戲班私行演唱之事。”[24]“新疆無戲班”的結論看上去似乎不容懷疑,以致于學界推測“禁戲高壓之下,內地戲班似全部東歸”[25],或得出“原存新疆之各內地戲班只能盡行返回內地,新疆之戲曲業顯然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26]的結論。事實恐非如此。
嘉慶二十年(1815)十二月至二十四年(1819)三月,原江西(略)令史善長因罪發遣烏魯木齊,在此地生活了三年多的時間,賜還后寫有一部《輪臺雜記》。書中記載:烏魯木齊“民重賽會,自三月東岳會起,(略)鎮殆無虛日,至十月朔嚴寒乃罷”。“三月仙姑娘娘會最盛,廟在漢城北,搭臺演秧歌。”“次則城隍會、觀音會,”還有文昌會等等。所描述的賽會之盛絲毫不亞于紀昀所記,但沒有明確說該地演劇,唯一提到的“演秧歌”是否就是演戲尚需進一步考察。該書又云“口外例不演戲,年終匯奏,并咨軍機處。然商貨泉流,客民霧集,游手者不少。有秧歌部、女檔部,秧歌樂神,女檔娛賓。作升平之鼓吹,豢邊徼之窮黎,亦官法所不禁,采風所不廢也”[27]。“口外”是新疆的俗稱,“例不演戲”“年終匯奏”“咨軍機處”說的顯然是嘉慶十三年的禁戲令和各處須年終匯奏禁戲情況之事。“女檔娛賓”,女檔和女檔部自是娼妓和妓館的別稱。漢民有賽神時演戲的習俗,則樂神之秧歌和秧歌部指的應是唱戲者和戲班。再聯系到道光十八年(1838)成瑞所說“新疆禁止優戲,民間報賽,皆唱太平秧歌”[28],從而可以確定史善長所說的“演秧歌”和成瑞口中的“唱太平秧歌”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戲曲演出的諱稱。
《輪臺雜記》不但指出烏魯木齊留有戲班,而且還可以公開在廟會上演出。書中還記載了秧歌部戲女福兒被某大員豢養之事。[29]雍正、乾隆和嘉慶三朝曾多次發布諭令,禁止外官蓄養優伶和戲班,[30]而此大員竟置禁令于不顧。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句“亦官法所不禁”,朝廷明明有嚴厲的禁令,此處卻說官法不禁。而且史善長在烏魯木齊的三年期間,都統每年都向清廷奏報說該處沒有戲班容留。[31]
除烏魯木齊外,史善長的詩歌和歸程筆記當中還透露出烏魯木齊都統管轄的阜康以及濟木(略)妓館和酒肆茶坊又多是演戲之所。
道光十三年(1833),薩迎阿由烏什辦事大臣調任哈密辦事大臣,上任途經烏魯木齊時所作的詩中有“花欄粉黛開千戶,水磨亭臺起六家”的句子。“花欄”句下注:“漢城花巷有女如云”[34]。此花巷之女當中應有為數不少的優伶。經過吐魯番時,賦詩描繪當地“燈火攤錢(略),管弦呼酒上春臺”[35]。“春臺”即戲臺,“管弦”“春臺”二詞表明該地應該也有戲曲活動。吐魯番時為直隸廳,亦屬烏魯木齊都(略)。
嘉慶禁戲令發布之初的幾年里,新疆各地可能確實遵照禁令驅逐了戲班,由此導致暫時無戲班的局面。嘉慶十七年(1812)烏魯木齊領隊大臣恒杰在中秋節當天傳喚兵丁進署喝酒唱曲一案,[36]似能支撐這一推論:如有專業戲班,何至于傳喚兵丁?但從史善長的記載來看,這種無戲班的局面并未持續幾年,地方官對復來的戲班采取了默許態度,并未如實奏報和加以驅逐,戲曲活動也未受到嚴格限制,仍可以公開演出。
史善長將戲曲稱為“秧歌”,戲班稱為“秧歌部”,成瑞稱戲曲為“太平秧歌”。除此之外,也有將戲曲稱作“太平歌”的:道光十九年(1839),遣戍烏魯木齊的黃濬所作的詩中有“笙歌多在南梁上,且逐裙衫作浪游”的句子。自注曰:“南梁在迪化南門外,地多祠廟,太平歌叢集之所。”[37]可見禁令之下的戲曲演出并未絕跡,只是不再以唱戲相稱,而是改稱為“演秧歌”“唱太平秧歌”或“太平歌”。史善長所說的“秧歌”就是“太平秧歌”的簡稱,據此“太平秧歌”“太平歌”之類的稱呼早在嘉慶晚期就有,并非如有些學者所說遲至道光中葉才出現。[38]
總之嘉慶十三年的這次查禁戲曲并未達到預期效果,烏魯木齊的戲曲演出仍相當繁盛,甚至有大員違禁蓄養優伶,其所屬的阜康、濟木薩、吐魯番等地可能也有戲班和戲曲活動。
三道光十八年的禁戲令及光宣年間的戲曲政策
戲曲和戲班的改頭換面未能逃過清廷的耳目。道光十八年(1838),喀喇沙爾換防游擊伊林保控告此處辦事大臣海亮侵蝕公項,私役兵丁署內唱戲、傳喚倡優等罪名。[39]清廷在命人查辦此案的過程當中發布了第二道禁戲令:
諭軍機大臣等:(略)為邊防要地,該處將軍、大臣等固當廉明表率,即員弁、兵丁亦應操防練習,屏斥嬉游,方為有備無患。朕聞該處近多演劇游戲,以唱太平歌為名,彩服登場,歡呼取樂,竟有兵丁扮作戲劇,蕩檢逾閑,不成事體。兵弁習勤講武,日久自成勁旅,似此違例玩法,尚安望其折沖御侮耶?著奕山、廉敬、恩特亨額等細加訪察,如有此種惡習,立即嚴行懲辦,毋使相沿日久,漸染澆風,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40]
這道禁戲令說明此前嘉慶禁戲的效果并不理想:新疆仍有戲曲活動,(略),而且還有駐軍參與演戲的行為。此諭有兩層意思,一是繼續禁止以唱太平歌為名的演劇活動,二是尤其要禁止兵丁演戲,包括滿洲兵也包括綠營兵。諭旨中點名的奕山時任統轄全疆的伊犁將軍,廉敬任管轄北疆(略)的烏魯木齊都統,恩特亨額任總理南八城事務的葉爾羌參贊大臣。道光本意是要通過他們傳達給各自所轄的駐扎大臣(略),進而覆蓋全疆,但從結果來看,這道諭令只傳到了奕山駐扎的伊犁和恩特亨額駐扎的葉爾羌兩處,未能覆蓋兩大臣所轄的(略)域,而且連諭旨當中點名的廉敬任都統的烏魯木齊都沒有傳達到,遑論其所(略)。
自該年起新疆各地奏報的禁戲折有了一些內容(略)別:接到道光禁戲諭令的伊犁和葉爾羌在奏報時先引嘉慶十三年禁戲諭旨,再引道光十八年禁戲令。因為需要稽查兵丁,所以兩處負責稽查的官員也有變化:伊犁負責查禁的官員除管理民事的撫民同知外,還加入了管理滿營的領隊大臣、協領以及管理綠營的總兵。[41]葉爾羌也相應對稽查官員作了調整,綠營參將繼續負責稽查地方有無戲班,另委印房章京訪察有無兵丁扮作戲劇情事。[42]而烏魯木齊和其他各地因沒有收到道光十八年的禁令,奏報仍然沿襲嘉慶十三年禁戲折的格式和基本內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大量新疆各地駐扎大臣奏報的禁戲折,最早是嘉慶十三年,最晚延至同治二年(1863)。[43]奏報的形式有專折具奏,也有另片附奏。奏報時間一般在當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也有個別提前至十月底或延至次年正月。皇帝的批示絕大多數只是“覽”或“知道了”寥寥數字,極少數有一些勉勵的話語,如“仍應認真稽查,毋稍疏懈”[44]。道光十八年以后各地奏報的結果仍是每年本境并無戲班,伊犁、葉爾羌還附加奏報說沒有兵丁唱戲。但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仍先以烏魯木齊為例,前引成瑞、黃濬的詩作及詩注已經說明道光禁戲當年和次年,該地仍有戲曲演出活動。此外黃濬遣戍烏魯木齊期間(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六年)所作的《紅山碎葉》對此處戲曲有更為細致的記載:當地有大鳳班、小鳳班、江東班等數個戲班,其中大鳳班還是某鳳姓旗員所蓄。并說:“口外諱言‘戲’,以有厲禁,謂之‘太平歌’。”“俗以六月六日大會于紅山嘴之火神廟,臺閣戲劇,鉦鼓喧闐,士女云集。”當地官吏每年在城外智珠山舉行“案牘會”,“演戲于山下沙磧上。”“正(略)最盛,例禁演戲,避其名謂之‘太平歌’。”[45]
刊于咸豐元年(1851)、反映道光時期之事的唱詞《出口外歌》中說“出口人”到烏魯木齊后,經常“到午間往大街去把戲看”,而且結識的當地妓女也提到常常看戲。[46]咸豐元年倭仁出任葉爾羌幫辦大臣,行至吐魯番勝金臺時看到“村墟演劇酬神”[47]。咸豐二年遣戍烏魯木齊的楊炳堃走到木壘,“適屆會,市演劇酬神,信步至會,周游一過,”[48]留有“煙火千(略)廛,踏歌聲里奏神弦”[49]的詩句。吐魯番和木壘同屬烏魯木齊都統管轄。
再看伊犁的情況。林則徐曾因禁煙而遣戍伊犁惠遠城,日記當中多次記載該地的戲曲活動。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元宵節“市上有演臺閣、唱秧歌者”,“唱秧歌”即唱戲的諱稱。二月十二日,惠遠城西關外“見鄉間演劇,觀者如堵”。十五日,北關外“見大神廟中演劇”。十九日攜兩兒“同赴大士廟觀劇”[50]。
南疆喀喇沙爾和葉爾羌也有戲曲演出。道光二十五年林則徐赴南疆勘荒,六月十九日見喀喇沙爾西門外“以觀音佛誕演劇,觀者如堵”[51]。咸豐十一年(1861),葉爾羌參贊大臣英蘊因母親過壽,將舊有太平社藝人叫至私舍演戲。[52]此“太平社”應得名于“太平歌”,亦是戲班。
黃濬曾批評烏魯木齊的戲曲表演“曲目鄙俗、情節支離,裝男腳色則跳舞為能,裝女腳色則面目可丑,直不可以言‘戲’”[53]。有學者據此認為:禁令之下“當地應該并沒有內地那樣非常正規和專業的戲班存在,此類所謂之戲或許只是當地民人一種較為原始粗俗的娛樂形式。”或因此推論“‘太平歌’與乾嘉時期當地戲班的規模、戲曲表演形式已很大不同,已偏向于‘舞蹈’表演”[54]。筆者認為黃濬的評價出自個人喜好,并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結論。黃濬乃浙江臺州人,出仕后又一直在江西為官,兩省都流行曲詞典雅、行腔婉轉、表演細膩的昆曲,與新疆流行的曲子戲在曲目名稱:(略)
筆者也不贊同“鑒于禁戲的余威,戲班的主要活動轉至城外關(略)”和“因(略)禁戲的嚴格,一些戲班似乎(略)轉移至村落”[55]的觀點。前一說法引用黃濬“南梁在迪化南門外,地多祠廟,太平歌叢集之所”之語來論證。祠廟前唱戲是為酬神,只要空間條件允許,唱戲自然要在祠廟前進行,南梁既多祠廟就定是太平歌叢集的地方,這跟禁不禁戲無關。而且古(略)內部空間一般比較狹隘,只會建設少數重要的壇廟,多數祠廟會建于城外。后一說法引用倭仁在吐魯番勝金臺見到的“村墟演劇酬神”來證明,勝金臺是吐魯番境內的一處軍臺,確是屬于村落等級的居民點,但村落唱戲未必是因為城鎮禁唱。戲班是賣藝謀生,何處請邀去何處,到村落唱戲與城鎮禁唱沒有必然關聯。
以上幾種觀點都是在所掌握史料缺乏反證的情況下,基于禁戲令的存在和奏折“無戲班”的結論作出的推測,夸大了禁戲令的影響。事實上此次禁戲的覆蓋面和力度遠不及嘉慶十三年那次,效果也不如之。不但烏魯木齊及其所(略)戲曲繼續存在和公開演出,而且伊犁、喀喇沙爾、葉爾羌等地也出現了戲班和戲曲活動的記載,表明新疆戲曲非但沒有禁絕,反而得到進一步蔓延發展,并且仍有官員違禁蓄養戲班。
清廷最后一次重申新疆禁止演戲是同治即位之初。[56]同治三年(1864)起新疆陷入十余年的戰亂之中,受兵燹影響,未見戲曲活動的記錄。光緒初年清軍收復新疆,隨著社會環境趨于安定,戲曲活動逐漸再次勃興。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建省后清廷全面禁止該地演戲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解除,而不是目前學界所說的“削弱”或“松弛”[57]。
光緒十六年(1890),古城城守尉德勝控告鎮迪道道員恩綸在忌辰之期演戲宴客。陜甘總督楊昌濬調查后匯報,恩綸并未在忌辰之日演戲宴客,并說:“新疆雖遠處關外,凡遇忌辰齋戒從不演戲,至今例禁綦嚴。”[58]宣統二年(1910),御史瑞賢參劾新疆布政使王樹枏于光緒“國服未闕”之期,藉母壽張筵演劇等罪名。陜甘總督長庚派人調查后回奏:王樹枏為母祝壽唱戲屬實,但一接到光緒駕崩的電文就立即停止,建議此項罪名“應免其置議”[59]。后王樹枏雖被開缺調京,但并非演戲所致。[60]兩份奏折不但直言新疆存有戲班,而且被控告的兩人一因未在忌辰演戲、一因聽聞皇帝駕崩即停止演戲而免于懲處,表明清廷的全面禁戲令已經解除,新疆只需與其他省份一樣遵守忌辰齋戒之日不演戲的規定即可。
以上是官方組織的演戲案例,再來看民間的戲曲活動情況。1902年德國人卡恩·德雷爾(CarenDreyer)“考察”吐魯番,行至烏蘇時記載:“當我們進城的時候,窄(略)場上正在唱戲,真是一道色彩絢麗的美景!”還說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途中的客棧有時候會滿員,“因為商人、中國官員或者走村串巷的戲子們都會住在這里。”[61]表明戲曲活動在民間也較為普遍。
有觀點認為道光十八年以后至清朝滅亡,新疆一直全面禁戲,故而將湘軍收復新疆以后的這段時間合并討論,在列舉了烏魯木齊太平歌、勝金臺演劇酬神以及咸豐至宣統期間的數則戲曲演出案例之后,得出本階段戲曲“較之乾隆后期至嘉慶前期,顯然大為衰頹”的結論,并認為“這種種情形,自然不能歸為載記的缺失,而應歸因于西(略)驅逐戲班東歸內地這一事實”[62]。前文已經論證,道光十八年至同治戰亂前,新疆戲曲仍在繼續發展,光宣時期禁戲令解除,新疆戲曲因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今天的新疆戲曲事業正是植根于這個時期。[63]說其大為衰頹恐與史實不合,因缺乏史料而再次夸大了禁戲令的影響。
四結語
清軍入關后統治者為了保持本族文化、維持軍事優勢,對本族接觸漢文化多有限制。就戲曲領域而言,清帝曾多次發布諭令,限制或禁止旗人聽戲、唱戲。這些禁令并非只針對新疆,京師對戲曲的管控更嚴,京師之外的陪都盛京以及西藏也有限制戲曲活動的諭令,只是不似京師和新疆這般嚴格。無論是乾隆限戲令,還是嘉道禁戲令,都以防止駐軍腐化、維持戰斗力為出發點,反映出統治者對西北軍政和邊防的重視。統治者對可能影響軍隊紀律、習氣和戰斗力的行為加以限制或禁止,本無可厚非,但如何在達到目的的前提下避免擴大化而“傷及無辜”,體現的則是統治者的眼界和智慧。流入新疆的內地民眾只有通過移植、復制包括戲曲在內的故鄉文化記憶才能對新環境產生認同和依賴,進而“各安生業”,維持邊疆穩定。乾隆能認識到戲曲等傳統文化對于新疆內地移民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意義,故能(略)別地加以對待,而繼任的嘉慶、道光卻只知變本加厲地嚴禁和取締,從而造成朝廷法令與民眾習俗的嚴重沖突。
必須承認,嘉道兩次禁戲令的發布對新疆戲曲活動的影響是顯著的,它迫使戲曲活動由公開轉入“隱秘”,(略)活動,(略)徑自由傳播和發展。在這個前提下重新審視禁戲令的實際、具體效果,其對新疆戲曲發展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此前可能被夸大了。從兩次全面禁戲后新疆的戲曲演出情況來看,禁令除了頒布之初的短時間內可能有效外,總體上并未達到預期目的,戲曲和戲班改頭換面后繼續公開活動,且有擴大蔓延的趨勢,還有官員違禁唱戲,甚至蓄養優伶,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新疆的戲曲表演水平發生了衰頹。
考察清代新疆的戲曲活動必須(略)域差異。哈密、吐魯番因地處要沖,流寓和行經的內地人口較多,南八(略)的戲曲活動遠沒有內地人口聚集的北疆,尤其是烏魯木齊及其所(略)發達。考察禁戲令的影響時也應考慮這一差異,南八城某些偏遠的地方,如和(略)可能確實長期沒有戲曲活動,禁與不禁差別不大;但北疆不同,禁令前后戲曲活動的變化更能體現出查禁的效果和影響,因此更具有樣本意義和說服力。這樣的典型樣本首推烏魯木齊及其所(略),次則巴里坤、伊犁。
盡管本文補充了不少禁戲令下戲曲演出的資料,但展示的仍然不是清代新疆戲曲活動的全部面相。因為禁令的長期存在,我們無法從官方口徑獲得更多有價值的信息,只能主要依賴游歷、為官或遣戍新疆者的私人筆記、日記、詩歌等材料。城鎮人口集中,賽神演劇較多,還有專門的酒肆戲園,而其他較為偏僻的地方一般逢節慶才會演出戲曲,不一定被西行東歸者遇到,況且戲曲演出在內地很常見,即使遇到也不一定會記載下來,所以實際上的戲曲演出活動應該比本文列舉的還要多,這就更進一步說明禁戲令的不理想。真正對清代新疆戲曲活動造成致命打擊的并非禁戲令,而是同光年間的戰亂。晚清新疆禁戲令解除,新疆戲曲活動由此進入了自由發展階段,今日新疆的戲曲事業正是奠基于此。從建省前后清政府對待新疆戲曲活動的態度變化,可以看出新疆建省后除行政制度與內地趨同之外,文化政策也有了一體化的調整。
滑動查閱注釋
[1]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州縣建置視角的清代新疆治理研究”((略):20BZS146)階段性成果。刊出時吸收了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與《西域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2025年西北邊疆研究工作坊:清代新疆的‘治’與‘安’”會議上專家提出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了修改,在此表示感謝。
[2]賈建飛:《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85~194頁;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5~31頁。
[3]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63~279頁。
[4]方華玲:《論清代的禁戲制度》,《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4期,第39~41頁。
[5]〔清〕王樹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77頁。
[6]《奏聞巴里坤城迤西四十余里之花莊一帶開水渠增墾荒地情形》,乾隆三十年十月十七日陜甘總督楊應琚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朱批奏折,檔號:“故宮”047389。
[7]〔清〕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卷一《新疆紀略上》,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清刻本,第6頁。
[8]〔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載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2~187頁。
[9]《清高宗實錄》卷九九一,乾隆四十年九月癸酉。
[10]《奏遵旨查禁伊犁駐防滿洲兵丁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初一日伊犁將軍伊勒圖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25;《奏遵旨禁止塔爾巴哈臺八旗官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初八日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慶桂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11;《奏遵旨禁止葉爾羌駐防滿洲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二日葉爾羌辦事大臣瑪興阿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38;《奏遵旨嚴禁烏什滿洲官兵飲酒唱戲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烏什參贊大臣綽克托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033。這只是現存奏折,應還有一些奏折沒能保存下來。
[11]《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一,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寅。
[12]《清高宗實錄》卷一○六九,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乙亥。
[13]〔清〕趙鈞彤:《西行日記》,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略),1996年,第155頁。
[14]〔清〕王大樞:《西征錄》卷四《廉五酒坊》,國家圖書館館藏民國抄本,(略):地800/8547,無頁碼。王大樞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抵達伊犁戍所(見同書卷二),開設酒坊的時間為“予來伊犁之二年”,即到戍后第二年。
[15]《奏為綏定城民王貴珍扎斃同班龔明擬絞監候事》,嘉慶十三年三月初五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16]《奏為遵旨駐防官兵查禁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三月初五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17]《清仁宗實錄》卷九四,嘉慶十三年四月丁卯。
[18]《奏為遵旨通飭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六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此處所引嘉慶諭旨為該折抄引,諭旨發布時間為嘉慶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19]《奏為遵旨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五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20]《奏為遵旨驅逐伊犁等處戲班事》,嘉慶十三年五月初八日伊犁將軍松筠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21]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0~273頁。作者所引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多數也有收藏,限于文章篇幅,各地驅逐戲班詳情不再摘引奏折一一敘述,具體內容可參閱此文。
[22]十一個(略)是伊犁、塔爾巴哈臺、烏魯木齊(兼轄巴里坤、吐魯番、庫爾喀喇烏蘇等地)、哈密、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
[23]“南八城”指地處天山以南的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屬喀什噶爾)、和闐等八城及其所(略)。
[24]《奏為查明新疆各屬地方并無戲班演唱事》,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6-006。《奏為遵旨烏魯木齊并無戲班演戲事》,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5-047。
[25]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4頁。
[26]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頁。
[27]〔清〕史善長:《輪臺雜記·上》,載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61冊),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508~510頁。
[28]〔清〕成瑞:《輪臺雜詠》,見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7頁。
[29]〔清〕史善長:《輪臺雜記·上》,載董光和,齊希編:《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第62冊),第72頁。
[30]〔清〕托津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九《吏部·處分例·居官燕游》,嘉慶二十三年內府刊本,第15~17頁。
[31]《奏為遵查新疆地方本年并無容留戲班演戲事》,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高杞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3-024;《奏為嘉慶二十二年份新疆地方并無容留戲班演唱情形事》,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烏魯木齊都統慶祥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1-012;《奏為遵旨新疆地方查禁戲班事》,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烏魯木齊都統慶祥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7-015。
[32]〔清〕史善長:《至阜康》,編寫組:《歷代西域詩選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8頁。
[33]〔清〕史善長:《東還紀略》,清光緒刻本,第3頁。
[34]〔清〕薩迎阿:《烏魯木齊》,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47~348頁。
[35]〔清〕薩迎阿:《土魯番》,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47頁。
[36]《奏為遵旨審明烏魯木齊領隊恒杰與兵丁飲酒彈唱并私用馱價剩銀一案按律定擬事》,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烏魯木齊都統興奎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9-045。
[37]〔清〕黃濬:《中元后二日曉霽》,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78頁。
[38]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5頁。
[39]《奏為喀喇沙爾換防游擊伊林保稟揭該城辦事大臣海亮等各劣款請派欽差大臣查辦事》,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40]《清宣宗實錄》卷三一三,道光十八年八月庚辰。
[41]《奏為伊(略):(略)。
[42]《奏為查明葉爾羌境內并無戲班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奏,一史館藏錄副奏折,檔號:(略)。
[43]《奏報新疆地方并無容留戲班及演戲之事》,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伊犁將軍常清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錄副奏折,編號:“故機”095454。
[44]《奏為境內查禁戲班事》,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庫車辦事大臣承芳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5-015。
[45]〔清〕黃濬:《紅山碎葉》,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民俗文獻》第118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103~104、107、111~112、126頁。
[46]張貴喜,張偉編著:《山陜古逸民歌俗調錄》,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55~56頁。
[47]〔清〕倭仁:《莎車行紀》,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第497頁。
[48]〔清〕楊炳堃:《西行記程》,吳豐培主編:《(略)資料匯鈔(清代部分上)》,第454頁。
[49]〔清〕楊炳堃:《過木壘河》,星漢編著:《清代西域詩輯注》,第394頁。
[50]周軒,劉長明編注:《林則徐新疆資料全編》,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88~291頁。
[51]周軒,劉長明編注:《林則徐新疆資料全編》,第336頁。
[52]《清穆宗實錄》卷一○,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丙申。
[53]〔清〕黃濬:《紅山碎葉》,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民俗文獻》第118冊,第104頁。
[54]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頁;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6頁。
[55]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6、277頁。
[56]《清穆宗實錄》卷二,咸豐十一年八月己未。此時咸豐已逝,(略)。
[57]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8頁;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頁。
[58]《奏為查明甘肅鎮迪道恩綸被參各節事》,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六日陜甘總督楊昌濬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7-094。
[59]《奏為遵旨查明新疆布政使王樹枬被參各節復陳事》,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陜甘總督長庚奏,一史館藏朱批奏折,檔號:(略)0-126。
[60]《宣統政紀》卷五四,宣統三年五月己亥。
[61]〔德〕卡恩·德雷爾著;陳婷婷譯:《絲路探險:1902—1914年德國考察隊吐魯番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0、36頁。
[62]賈建飛:《人口流動與乾嘉道時期新疆的戲曲發展》,《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31頁;彭秋溪:《清代新疆查禁戲曲演出考》,《戲曲研究》2018年第2輯,第275~278頁。
[63]徐玉梅主編:《新疆曲子》,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新疆電子音像出版社,2015年,第1~45頁。
(作者單位:(略)
編校:楊春紅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霞
掃碼關注我們微信:(略)
郵箱:(略)
|
關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上文為隱藏信息僅對會員開放,請您登錄會員賬號后查看,
如果您還不是會員,請點擊免費注冊會員
|
||||||||||
最新招標采購信息
更多烏魯木齊招標采購信息
熱點推薦
熱門招標
熱門關注
- 塔城招標網
- 哈密招標網
- 和田招標網
- 阿勒泰招標網
- 克孜勒蘇招標網
- 博爾塔拉招標網
- 克拉瑪依招標網
- 烏魯木齊招標網
- 石河子招標網
- 昌吉招標網
- 吐魯番招標網
- 巴音郭楞招標網
- 阿克蘇招標網
- 喀什招標網
- 伊犁招標網
- 阿拉爾招標網
- 圖木舒克招標網
- 五家渠招標網
- 北屯招標網
- 鐵門關招標網
- 雙河招標網
- 可克達拉招標網
- 昆玉招標網
- 隆化縣農業農村局
- 合肥大學
- 邵陽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 貴州盤江電投發電有限公司
- 葉城縣夏合甫鄉小學
- 南沙區人民政府
- 馬鞍山教育局
- 廣州市電化教育館
- 湖南省體操運動管理中心
- 常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武進分中心
- 重慶南桐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 南通市城鎮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西安高壓電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 婺源縣自然資源局
- 國能山東置業有限公司
- 廣西|壯族自治區藥械集中采購網
- 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隊
- 桂陽縣政務服務中心
- 云南紅塔藍鷹紙業有限公司
- 北京郵電大學世紀學院
- 洛浦縣阿其克鄉衛生院
- 江西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
- 榆樹市水利局
- 隆化縣財政局
- 烏魯木齊市烈士陵園
- 成都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
- 航天萬源實業有限公司
-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保健中心
- 青島市黃島區交通運輸局
- 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金隅臺泥(代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 江蘇怡寧能源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東莞市應急管理局
- 中冶沈勘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 沈陽市蘇家屯區房產局
- 蘇州太湖新城吳中管理委員會
- 寧夏政府|采購網招標公告
- 安徽省工程建設招標采購網
- 四川省鐵路建設有限公司
- 長沙市政府采招標公告
- 南京市招投標協會
- 龍城區應急管理局
- 合肥百姓網
- 龍巖醫療器械采購平臺
- 堡壘機招標
- 高青縣政務服務中心
- 一汽電子招標
- 吉林省政府采購招標平臺
- 山東財經大學
- 福建工程學院管理學院
- 全球采購中心
- 漳州市政務服務中心
- 煙臺開發區招標公告網
- 安徽采購國產醫療器械
- 樊城區人民政府
- 承德市平泉市
- 延邊州人民政府
- 招標|資源網下載
- 蘭陵縣教育局
- 縉云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上海復星長征醫學科學有限公司
- 漯河公共資源交易網
- 岳陽縣人民政府
- 北京裝飾裝修招標信息
- 召陵區政務服務中心
- 安吉縣政府采購中心
- 濟南招標公司
- 香河縣|招投標中心
- 陽光招標網
- 諸暨招標網
- 山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招標信息
- 合川市建設信息港
- 宿城區人民政府
- 陵川縣|招投標中心
- 建設資源交易中心
- 安陽縣教育局
- 安化縣人民政府
- 金壇經濟開發區
- 遼寧省招標投標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