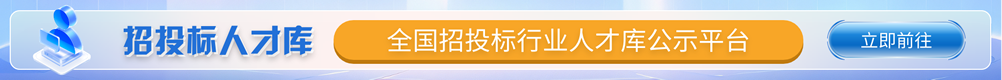全部選擇
反選
反選將當前選中的變為不選,未選的全部變為選中。

華北
華東
華中
華南
東北
西北
西南
其他
取消
確定
王圣琳 | 吐魯番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天山縣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再整理
所屬地區:新疆 - 吐魯番 發布日期:2025-09-02| 所屬地區: | 新疆 - 吐魯番 | 招標業主: | 略 登錄查看 | 信息類型: | 其他公告 |
| 更新時間: | 2025/09/02 | 招標代理: | 略 登錄查看 | 截止時間: | 略 登錄查看 |
咨詢該項目請撥打:15055702333
發布地址:(略)
來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3期
吐魯番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再整理[1]
王圣琳
內容提要吐魯番所出武周天授二年高元禎職田案卷是研究唐代田制與地方行政制度的珍貴史料,仍有再整理的必要。《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新刊布的一組文書無法拼合,3件殘片至少分屬2件辯文,包含1件西州都督府勘問原告唐建進的辯文和1件牒辯。《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實際由“康進感狀”與“倉曹狀”兩部分構成,后者與《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屬同一件狀文,而能與之綴合的《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則是這件狀文的判白。拼合后的文書宜重新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
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230號墓出土一批武周天授二年(691)的文書,整理者指出文書系西州都督府勘檢(略)六(72TAM230:68);最后,文章探討了高元禎案的原委,進而關注到案卷所涉逃死田問題。[4]
前輩學者的研究已有很大推進,但高元禎案卷仍有再整理的空間:第一,新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收錄另一組殘片,可補充新信息;第二,部分文書在性質、綴合等方面仍有疑義。下文嘗試從上述問題出發,對高元禎案卷作新的整理研究。
一
結合前輩學者論述,總結案情如下:(略)安昌城人唐建進向西州都督府告(略)主簿高元禎侵占逃死、戶絕、還公地,天授二年一月至四月西州都督府在安昌、南平兩城開展調查,被調查者除原告唐建進和被告高元禎外,還有合城老人、城主、渠長、知田人、知水人等人員。因文書殘缺,無從得知后續進展,陳國燦先生也只能推斷高元禎是以職田名義侵占逃死、戶絕、還公地,并認為這是反映武周時均田制出現弊端的典型案例。
高元禎案卷相關文書,除陳國燦先生揭示的22件外,還有3件殘片,刊布于朱雷先生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一書。3件殘片皆無墓葬信息、(略),朱雷先生據紙質、內容、格式、筆跡等要素判斷這組文書可以拼合,并指出這組文書與高元禎案卷的關聯,進而將之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謹移文書圖版(圖1)并朱先生錄文如下(本文武周新字皆改為通行漢字,“[殘片A/B/C]”系筆者所加)。[5]
圖1《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所刊《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圖版
從文書樣式判斷,3件殘片皆是辯文。“辯”在唐代是種文體,用于回答官府訊問,節引黃正建先生總結的“辯式”如下。
[1](辯者)姓名、年齡、畫押(指印);[2]訴訟標的(此項不必須有);[3]某(辯者)辯:被問(下列被問事項);[4]仰答者;[5]謹審:(下列回答的內容,往往以“但”字開頭);[6]被問依實謹辯(后面往往有負責處理案卷官員的署名);[7]年月日。[6]
在前述高元禎案卷的22件文書中,至少有10件辯文,樣式大體分為兩類。一類符合黃正建先生總結的“辯式”,如西州都督府勘問李申相、康進感、郭文智等人的辯文。[7]
另一類以西州都督府勘問高元禎的辯文為例:[8]
文書第4行“亦不回換粟麥”之前的內容對應“辯式”第[5]項;之后第4、5行的內容依次對應第[6][7]項。第4行的“感”應是西州都督府“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9]第5行署名是“(略)主簿高元禎”,知文書是西州都督府倉曹勘問被告高元禎的辯文。這件文書與前一類樣式稍異,主要表現在第[6][7]項的“被問依實謹辯”“(某)辯”為“被問依實謹牒”“(某)牒”取代。[10]
《唐六典》云“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11]可能因為辯者身份不同,辯有“辭辯”“牒辯”兩類樣式。就高元禎案卷而言:辭辯的使用者是庶人,而李申相、康進感、郭文智等人的身份是知水人、知田人,則雜任層、雜職層或也使用辭辯;[12]牒辯的使用者應具有官人身份,如主簿高元禎。另參考阿斯塔那239號墓所出《唐景龍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龍四年(710)正月西州(略)墓所出《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謙、薛光泚、康大之請給過所案卷》第1~10行[73TAM509:8/4-1(a)]2件保存相對完整的牒辯,[13]可對唐代“辯式”補充如下。
對照“辭辯”“牒辯”樣式可知,《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收錄的[殘片A]與[殘片B][殘片C]應不是同一件文書。
首先,[殘片A]是原告唐建進的辯文。原22件殘片中也有一件文書被整理者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14]據首行“□□辯被問建進若告主簿營種還公”知,文書確為辭辯。只不過首尾皆殘,可以判定辯者身份的第[1][3][7]項信息皆不完整,所以,文書中雖有“建進”,但無法認定唐建進就是辯者。
而[殘片A]第1行對應“辯式”第[1]項,系辯者的姓名、年齡與指印,知本件辯者確為唐建進。第2行對應“辯式”第[3]項,應是唐建進被問之事項(參考高元禎案卷其他辯文,辯者信息與被問事項間皆無“訴訟標的”一項)。本行以“建進”開頭,可以再次印證辯者身份,只不過“(主)簿于安昌所種田是”前殘缺“被問”二字。據前引高元禎牒辯,唐建進所告應有兩項:一是營種“逃死、□(絕)戶田”,二是“回換粟麥”。另據他人證詞,所涉地域包括(略)轄下的安昌、南平二城。[15]西州都督府倉曹受理高元禎案,需執行“三審”“受辭”等程序,[16]這很可能是本件辯文的生成背景,換言之,相較案卷其他殘片,本件文書的時間可能更早。只可惜文書殘缺,缺少判定文書為辭辯或牒辯的關鍵證據,暫時還不能武斷地認為[殘片A]是辭辯。
其次,[殘片B][殘片C]樣式為牒辯。第3行“牒被問得建進”對應“牒辯式”第[3]項,屬辯者被問事項。第7行對應“牒辯式”第[6]項,是辯文的結句。
值得注意的是,[殘片A]與[殘片B]均包含辯者被問事項,格式重復,是二者分屬不同辯文的力證。
并且[殘片B]“得建進”,不似勘問唐建進的語句。阿斯塔那239號墓所出《唐景龍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龍四年(710)正月西州(略)處分田畝案卷》第64~65行:“牒辯被問得堂兄妻阿白辭稱云籍下田地訴有□得者。縣判準狀問者。”[17]辯者嚴住君之堂兄妻阿白向(略)呈辭,縣司則就此事勘問住君。與前者相似,“得建進”是指辯者接收來自唐建進的文書,故辯者不應是唐建進。加之二者字跡略有差異(尤以“種”字較明顯),[殘片A]與[殘片B]應不是同一件辯文。
而據“牒辯式”,[殘片B][殘片C]格式互補,存在屬同件文書的可能,其辯者可能有一定官職。據第6行的“今款連署”知,辯者可能不只一人。又第4、5行的“種地多納子”“催地子(第5行的‘’似為‘催埊’,之后筆劃或‘子’字)”等信息,說明這件牒辯可能涉及催征高元禎職田地子事。綜合以上信息[殘片B][殘片C]的辯者可能是西州都督府或(略)的官吏。
綜上,《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中原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的一組文書,無法拼合,[殘片A]與[殘片B][殘片C]至少分屬兩件辯文。[殘片A]是勘問唐建進的辯文,但不明辭辯還是牒辯,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殘片B][殘片C]均符合牒辯樣式,暫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
二
在唐建進向州府告發高元禎侵占逃死、戶絕田后,事態發生變化。唐建進突然失蹤,西州都督府遂要求(略)領送唐建進的妻兒、鄰保赴州勘問。記敘該事件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72TAM230:73(a),71(a);以下簡稱《妻兒鄰保牒》]是高元禎案卷的核心文書之一,但學界以往認識存在問題,謹移錄文如下。[18]
從定名判斷,整理者認為文書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知水人康進感等人所上牒文的尾部與西州倉曹下(略)的牒文,但上述判定存在問題。
整理者據“牒”“謹牒”等語詞,判斷第1~2行的殘文書是一件牒文。但唐代文書存在牒、狀語混用現象,以“牒,件狀如前,謹牒”結句者,已被學者考證為唐地方官府所用之狀文。[19]第3~8行是西州都督府處理上件狀文的文案:[20]第3~4行是長官“傑”的署名環節,“傑”即時任都督的王孝傑;[21]第5~6行是受付環節,本應由錄事與錄事參軍事分別執行受、付程序,但此時錄事出使,錄事參軍事亦不在任上,所以由博士“仁”檢校錄事參軍事;第7行并第8行的“十二日”是行判環節,“感”即“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總之,《妻兒鄰保牒》第1~7行(含第8行的“十二日”)分為兩段:第1~2行是康進感等人上西州都督府的狀尾,第3~7行(含第8行的“十二日”)是西州都督府處理狀文的文案,該案由倉曹具體負責。
第8~16行的文書,整理者認為是西州都督府倉曹下(略)的牒文。
首先,發件單位:(略)
其次,其性質是狀文而非牒文。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唐代牒文,除有與敦煌出土P.2819號《唐開元公式令》殘卷之“牒式”(牒式A)相似外,還有與《司馬氏書儀》所收元豐牒式(牒式B)相似者。《妻兒鄰保牒》第8行的“倉曹”是發件單位:(略)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符合第8~16行樣式的文書有3類。第一是帖文,[22]但帖文是一種下行文書,與《妻兒鄰保牒》文書上行的情形不符。
第二是以“牒,件檢如前,謹牒”“牒,件勘如前,謹牒”結句的文案,以斯坦因所獲《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Ast.Ⅲ.4.094)第29~42行為例:[24]
案卷第31~42行系神龍元年(705)三月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長行馬死馬案卷的一部分。案卷涉及兩起死馬事:先是一疋長行馬回至柳谷鎮南五里病死,柳谷鎮狀上州,兵曹判“皮雖檢到,肉價不來,牒所由征還”,此為案卷第4~19行反映的內容;[25]再是兩疋往使伊州的長行馬,醫療不損致死,由長行坊狀上州,都督鄧溫[26]判“檢何故”,此為案卷第20~30行反映的內容。[27]
兵曹遵照都督判,核檢上述兩疋往使伊州之長行馬的死因,確定“無他故”后,制作了第31~41行的文書。末尾除兵曹參軍、府等兵曹官吏署名外,主帥、槽頭、獸醫等長行坊相關責任人也要連署。[28]書訖上行都督處分,鄧溫判“付司”,文書交還兵曹,兵曹參軍程待判“帖槽出賣訖具上”。
總之,綜合吐魯番出土的其他相似文書判斷,第31~41行兵曹這件上行文書,本質仍屬西州都督府內部文案。這類文案的樣式與處理程式并不固定,卻都要審案官員判以“檢”,[29]“件勘如前”亦同理。但第7行的判詞是“連”,亦不符。
第三是狀文。赤木崇敏遍考敦煌吐魯番文書,檢出5件都督府(州、郡)內部由諸曹發出的上行文書,[30]發現唐令雖規定官府內部的上行文書(別局上于本局)使用刺文,[31]但這5件文書無一例外皆是狀文。[32]所以,《妻兒鄰保牒》第8~16行不僅契合狀文樣式,也與西州都督府內部諸曹上行文書的用例相符。
綜上,《妻兒鄰保牒》第8~16行應是一件西州都督府內部倉曹發出的狀文(以下簡稱“倉曹狀”)。
三
“倉曹狀”正文殘有三句:首句是倉曹“準都督判”,同時向(略)(略)令陽愻[33]發文,要求“差人領送”唐建進赴州;次句是倉曹收到“縣申”(當是解文)和縣令“通狀”,答復“追訪建進不獲”,倉曹(略)令“依前捉送”,但始終未有結果;末句是都督再次下令,要求“追建進妻兒及建進鄰保赴州”,并繼續“依前捉建進”。
同墓另有《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72TAM230:58/1(a)~58/4(a);以下簡稱“牒尾判”]與“倉曹狀”內容關聯緊密。[34]
“牒尾判”第1~7行保存相對完整:府司認為唐建進不會逃亡,并要求領送唐建進家口赴州,所述內容大體同于“倉曹狀”,但補充了一些細節。第8~9行雖殘,仍可憑所余筆畫稍作推斷。
第8行前3字似為“二年壹”(“年”字為武周新字,“壹”字大寫),“月”字后或為“起”字。第9行為詞尾,第3字殘有“讠”旁,或為“諮”字;[35]第4字所殘筆畫似為“義”字左下部分,第5字應為“白”字之左上部分。第9行末2字整理者釋讀為“二日”,但“二”字之上似仍有一橫,或為“十”字。總之,可對“牒尾判”第8~9行重新釋文如下:
在唐代文書處理程式中,判官判詞書寫的一般格式是“云云。諮。某白。某日”。[36]從“牒尾判”第9行的格式,并筆跡、內容判斷,“牒尾判”系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判詞(細審圖版,第4字“義”、第5字“白”之間尚余1字空間,或可依理推補康義感之“感”字)。
既然“牒尾判”“倉曹狀”內容高度相關,二者是何關系?回答此問題前應注意可與“牒尾判”綴合的另一件文書——《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72TAM230:72)。先移錄文如下:[37]
從簽署官吏“史孫行感”“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知,這件僅余尾部的文書,也由西州都督府倉曹發出(以下簡稱“倉曹文尾”)。并且有2點可證“倉曹文尾”能與“牒尾判”綴合。
第一,兩件殘片茬口耦合,從縫背無押署判斷,兩殘片系同一張紙。
第二,從“倉曹文尾”到“牒尾判”,是連貫的處理程式。“倉曹文尾”第3~7行是西州都督府的署名、受付環節,之后應是判案環節,此環節一般先由判官行判。據第7行的“付倉”可知,文書交還倉曹處理。而“牒尾判”剛好是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判詞,且“牒尾判”末行的“十二日”也與“倉曹文尾”署名、受付日期一致。
總之,“倉曹文尾”有較大概率可與“牒尾判”綴合。
明確“倉曹文尾”與“牒尾判”的關系,可進一步推知“倉曹狀”與“倉曹文尾”可能是同件文書。換言之,“倉曹狀”“倉曹文尾”“牒尾判”3件殘片可以拼合。
第一,“倉曹狀”與“倉曹文尾”闊度相近,書法筆跡一致,皆應出自倉曹史孫行感之手。
第二,從文尾署名與西州都督府的處理環節判斷,“倉曹文尾”也是西州都督府內部由倉曹發出的上行文書,這與“倉曹狀”情況相同。
第三,既然“倉曹文尾”與“牒尾判”可以綴合,則“牒尾判”應是“倉曹文尾”的判文。而“倉曹狀”又與“牒尾判”內容高度相關,說明“倉曹狀”“倉曹文尾”的內容很可能也有關聯。
第四,3件殘片的時間也可提供線索。復引《妻兒鄰保牒》第7~8行如下:
康義感在判“連,感白”后,將“十二日”簽在后件“倉曹狀”上(第8行),表明康義感很可能在行判前件“康進感狀”時,就已收到了完成付司、受付的“倉曹狀”。所以,“倉曹狀”付司、受付日期應不晚于十二日,行判日期也應與十二日相近。而“倉曹文尾”的付司、受付日期,“牒尾判”行判日期剛好同為十二日。
拼合后的文書也符合連貫的處理程式。第7行“連”的判白正是對“倉曹狀”的預處理。“連”作為吐魯番文書的常見判詞,是判官在判案前要求主典將同類文書粘連,留待一并處理的措施。“連”與“檢案”是相反的一組判詞,“連”一般要求主典粘連兩件未了結的文書,而“檢案”則要求主典將新到文書與此前了結的文案粘連。文書處理一般要經過署名、受付、判案、執行、勾稽、抄目6個環節,[38]完成抄目后的文案可視作了結的狀態。以大谷文書5839號《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為例(“[第4/5紙]”系筆者據《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所加)。[39]
大谷文書5839號由相連的6紙組成,[第1紙][第6紙]殘缺不全,[第2~5紙]保存完整。據抄目推測,[第1紙]應是西州都督府兵曹、法曹的請紙文書,殘有都督署名,錄事與錄事參軍受付的文案。這件請紙文書依次經過判官、通判官、長官的判署程序([第2紙]),及執行、勾稽、抄目的程序([第3紙]),到[第3紙]22行為止,兵曹、法曹請紙案已了。[第4紙]是件新文書,由(略)完整地呈現了官司向州府請紙的行政運作過程,[40]從中可以看出,“檢案”與“檢案連如前”相對應,是將新到文書與此前已了結的文案粘連。
“連”則要求主典粘連兩件未了結的文書。仍以斯坦因所獲《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圖2)為例。[41]
圖2Ast.Ⅲ.4.094《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局部)[42]
關于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事的行政運作過程,前文已有論述。上述引文由3部分構成:第1~3行是收件單位:(略)
總之,“連”與“檢案”均要求主典粘連文案,區別在于:“檢案”是將新到文書與已了結的文案粘接,主典署“檢案連如前”;“連”粘連的都是沒有經過完整處理程式的文書,主典無需署名。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判官在騎縫線附近署“連”的情況屬于特例。但正是因為經歷了“連”這一預處理的程序,判錄事參軍康義感得以在“倉曹文尾”后直接行判,即“牒尾判”反映的內容。
同樣經過預處理后直接行判的狀文,還有阿斯塔那188號墓所出《唐神龍二年(706)主帥渾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狀為處分馬料事》[72TAM188:82(a)]:[43]
對照前引狀式,從“狀上”“謹以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判斷,第5~11行的文書是唐神龍二年二月某營上西州都督府的狀文。狀文到達西州后,依次經過署名、受付、判案等環節,第16、17行的判詞雖簡短,從“某諮某白”的格式判斷,也與“倉曹文尾”“牒尾判”的情況相似,屬判官即刻行判的例證。之所以能即刻行判,是因為渾小弟狀在到達西州后先經過了預處理,即第1~4行的內容。第1行的“事”即第5~11行的渾小弟狀,主典在渾小弟狀前接一紙,寫明狀文到來這一情況,署名后交由判官行判,敬仁判“連”,即將渾小弟狀同其他文書作并案處理。完成這些預處理后,遂有第16、17行的判白。
總之,上文通過繁復考證旨在說明,從“倉曹狀”到“牒尾判”是連貫的處理程式,既符合唐代的行政運作原則,也能在其他吐魯番文書中找到相似例證。
綜合上述五點,“倉曹狀”與“倉曹文尾”有極大可能是同件狀文,而“牒尾判”就是倉曹在處理這件狀文時的判詞,拼合后的文書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圖3)。進而可復原行政運作流程如下:武周天授二年一月十一日,知水人康進感等人向西州都督府呈交了一件狀文,接到狀文后都督王孝傑與錄事司博士攝(檢)錄事參軍“仁”即日作出處理;大約在此前后,倉曹呈交了另一件狀文,內容是向都督匯報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相關事宜,狀文在十二日完成付司與受付的流程;倉曹在同一時間處理了這兩件文書,在完成粘連工作后,判倉曹參軍康義感于兩件文書粘接處判“連”并署上姓名、日期,并在狀末——“博士攝錄事參軍付倉”的后一行書寫判詞,判詞寫至“仰準長官處分,即”,一紙用盡,又續一紙。
圖3《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拼合圖
結論
唐代逃亡問題武后統治時開始嚴重,[44]浮逃戶等問題導致逃死、戶絕田大量出現,給予地方官僚侵占之機,這便是高元禎案產生的背景。這一時期,全國曾開展勘查田土、檢括戶籍的活動,[45]以應對百姓大量流移的社會情勢。所以,在天授初年革唐建周的“敏感時期”,發生侵占逃死、戶絕田的“敏感案件”,高元禎案不僅備受西州官府的重視,或許也會牽動更高層統治者的神經。從殘存的高元禎案卷看,本案持續時間較長、涉及人物眾多、情節發展曲折,所以相關文書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是探討唐代田制與地方行政制度的珍貴史料。
同時,這也增加了整理難度,尤其考慮到案卷“殘缺已甚”“不能銜接”的現狀。[46]而《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新收錄一組案卷殘片,朱雷先生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1~3),對重新整理高元禎案卷有重要意義。在案卷原有的22件殘片中,也有1件文書被整理者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但因判斷辯者身份的核心信息缺失,暫無法據“辯式”論定辯者為唐建進。收錄于《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的這組文書,3件殘片均為辯文:第1件殘片據“辯式”可確知,辯者為唐建進;但第1件殘片與第2、3件殘片存在格式重復的情況,應至少分屬兩件辯文;第2、3件殘片格式互補,存在同屬一件辯文的可能,辯者可能是西州都督府或(略)的官吏,性質為牒辯。因此3件殘片無法拼合,宜分別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據唐代官司受理“告言人罪”的規定,西州都督府受理高元禎案,需對原告唐建進執行“三審”“受辭”等程序,所以倉曹勘問唐建進的辯文或可視作高元禎案卷的開端。
但隨著原告唐建進的隱匿,案情迎來重要轉折,記錄該事件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72TAM230:73(a),71(a)]也是案卷核心文書之一。這件文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知水人康進感的狀文,二是西州都督府內部倉曹的上行文書。后者其實與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72TAM230:72)是同一件狀文,他們又能與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72TAM230:58/1(a)~58/4(a)]綴合,拼合后的文書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本案中被告高元禎乃(略)主簿,系從九品上官。[47]據《唐律疏議》“輒自決斷”條疏議引《獄官令》,“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斷徒及官人罪”,[48]又按明鈔本《天圣令》宋2條,“若官人犯罪,具案錄奏,下大理寺檢斷”,[49]因為官人犯罪的性質,高元禎案當交由大理寺等機構審理,但前期調查工作由西州都督府及(略)承擔。本件文書作為“具案錄奏”的重要依憑,反映了西州都督府行政運作的生動細節。
最后附新錄文于后,通過案卷文書的再整理,希望能對學界正確利用這批材料提供一些參考。
《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
《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
《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72TAM230:71(a)~73(a),58/1(a)~58/4(a)]
滑動查閱注釋
[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略):17ZDA183)的階段性成果。
[2]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0頁。
[3]李征、沙知、宋家鈺、陳國燦、楊際平、小田義久、李文瀾、趙呂甫、李方等先生曾對案卷文書有過討論,相關研究可參見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略),2002年,第133頁。此外還有齊陳駿:《簡述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職田的資料》,《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40~49頁;寧可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150~161頁;盧向前:《唐代西州土地關系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4~296頁;王曉暉:《西州水利利益圈與西州社會》,《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52~60頁;劉子凡:《唐前期西州(略)水利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第52~63頁;雷聞:《隋唐的鄉官與老人——從大谷文書4026〈唐西州老人、鄉官名簿〉說起》,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1~156頁;楊際平:《論唐、五代所見的“一田二主”與永佃權》,《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7頁;呂冠軍:《吐魯番文書中的“雙名單稱”問題》,《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第80~87頁;裴成國:《唐西州契約的基礎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42~58頁;趙曉芳,郭振:《唐前期西州鄰保組織與基層社會研究——(略)》,《敦煌學輯刊》2020年第2期,第91~107頁;魯西奇:《父老:中國古代鄉村的“長老”及其權力》,《北京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89~101頁等。
[4]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455~485頁;后收入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1~392頁。
[5]參見朱雷:《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巴蜀書社,2022年,第83頁。
[6]黃正建:《唐代法律用語中的“款”和“辯”——以〈天圣令〉(略)》,《文史》2013年第1輯,第261頁。
[7]西州都督府勘問李申相的辯文有2件殘片,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西州都督府勘問康進感的辯文有1件殘片,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4頁。西州都督府勘問郭文智的辯文有3件殘片,包含2件辯文,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墓之文書,也符合這種樣式。前者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6頁;后者錄文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43、144頁。
[8]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79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四卷,法藏館,2010年,図版八一。
[9]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有“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署名(詳后)。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
[10]大谷文書4908號勘問康才智的辯文也是這種樣式,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80、381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図版八。
[11]〔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條,中華書局,1992年,第11頁。
[12]渡邊信一郎認為外職掌中,除了流外官,雜任層和雜職層都由色役來征發,仍屬于百姓。這可能是雜任層、雜職層也使用辭辯的原因。參見〔日〕渡邊信一郎著;吳明浩,吳承翰譯:《中國古代的財政與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488頁。
[13]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叁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59頁;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268頁。
[14]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2頁。
[15]參見陳國燦:《唐西州的四(略)制》,劉安志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新探(第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29頁。
[16]明鈔本《天圣獄官令》宋29條載官司受理“告言人罪”的規定,雷聞先生據《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通典》卷一六五《刑法·刑制》等材料,參考宋29條,復原為《開元獄官令》第35條:“諸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并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略),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于審后判記,審訖,然后付司。……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參見雷聞:《唐開元獄官令復原研究》,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第623、624頁。
[17]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叁卷,第559頁。
[18]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0頁。
[19]中村裕一、赤木崇敏、吳麗娛、黃正建、包曉悅等學者都曾討論過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牒、狀語混用現象,目前仍有爭論。筆者認為,這類文書在唐前期能否稱為狀文,需要進一步討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文書在唐前期已具有比較穩定的文書樣式和應用范圍。為方便行文,依赤木崇敏的歸納,暫稱為“狀文”。參見〔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9頁。
[20]關于唐代文書的處理程式,可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9~363頁。
[21]參見李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11頁。
[22]關于唐代的帖式,可參見雷聞:《唐代帖文的形態與運作》,氏著:《官文書與唐代政務運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89~91頁。
[23]〔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第126、127、129頁。
[24]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52、253頁。
[25]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49~251頁。
[26]參見李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第12、13頁。
[27]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51、252頁。
[28]荒川正晴注意到長行坊發出的許多牒、狀有主帥與押官的聯名簽署,并認為主帥、押官等鎮守指揮官實質上干預了長行坊的運營和管理。參見〔日〕荒川正晴著;馮培紅,王蕾譯:《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25頁。
[29]參見劉安志:《關于吐魯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2018年第3期,第96頁。
[30]以年代為序,4件文書的發出單位:(略)
[31]參見〔日〕吉川真司:《奈良時代の宣》,氏著:《律令官僚制の研究》,塙書房,1998年,第216~218頁。
[32]參見〔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第143~145頁。
[33]細審圖版,原錄文之“懸”字應為“愻”字。
[34]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1頁。
[35]敦煌吐魯番唐代文書中“諮”字之“言”旁多已簡化為“讠”旁。參見劉安志:《關于吐魯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2018年第3期,第101頁。
[36]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第349頁。
[37]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
[38]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第329~363頁。
[39]錄文據榮新江,史睿主編:《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中華書局,2021年,第470~474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図版九。關于《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所見西州行政運作的研究,可另參見雷聞:《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唐代公文用紙》,氏著:《官文書與唐代政務運行研究》,第222~247頁。
[40]還可參見《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的其他殘片,如黃文弼文書H31號((略)據《黃文弼所獲西域文書》)、大谷文書5840號等。錄文并參見榮新江,史睿主編:《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第474~481頁。
[41]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48~252頁。
[42]圖片源自“國際敦煌項目”(IDP)官網,訪問鏈接:https://(略).D475D401B881/?return=%2Fcollection%2F%3Fterm%3D4.094,訪問日期:2024年5月12日。
[43]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26頁。(略)的研究,可參見孫繼民:《從渾小弟一組文書看唐代早期健兒制度的幾個問題》,氏著:《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6~80頁。
[44]唐長孺:《唐代的客戶》,氏著:《山居存稿》,中華書局,2011年,第135頁。
[45]參見陳國燦:《吐魯番舊出武周勘檢田籍簿考釋》,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12~328頁;陳國燦:《武周時期的勘田檢籍活動——對吐魯番所出兩組敦煌經濟文書的探討》,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29~370頁。
[46]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0頁。
[47]唐代(略)(略),下縣主簿為從九品上官。參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三〇“京(略)天(略)官吏”條,第752頁;《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7頁。
[48]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卷三〇《斷獄·輒自決斷》,中華書局,1996年,第2065頁。
[49]校錄本《天圣令》卷二七《獄官令》,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第327頁。
(作者單位:(略)
編校:宋俐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霞
掃碼關注我們微信:(略)
郵箱:(略)
來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3期
吐魯番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再整理[1]
王圣琳
內容提要吐魯番所出武周天授二年高元禎職田案卷是研究唐代田制與地方行政制度的珍貴史料,仍有再整理的必要。《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新刊布的一組文書無法拼合,3件殘片至少分屬2件辯文,包含1件西州都督府勘問原告唐建進的辯文和1件牒辯。《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實際由“康進感狀”與“倉曹狀”兩部分構成,后者與《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屬同一件狀文,而能與之綴合的《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則是這件狀文的判白。拼合后的文書宜重新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
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230號墓出土一批武周天授二年(691)的文書,整理者指出文書系西州都督府勘檢(略)六(72TAM230:68);最后,文章探討了高元禎案的原委,進而關注到案卷所涉逃死田問題。[4]
前輩學者的研究已有很大推進,但高元禎案卷仍有再整理的空間:第一,新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收錄另一組殘片,可補充新信息;第二,部分文書在性質、綴合等方面仍有疑義。下文嘗試從上述問題出發,對高元禎案卷作新的整理研究。
一
結合前輩學者論述,總結案情如下:(略)安昌城人唐建進向西州都督府告(略)主簿高元禎侵占逃死、戶絕、還公地,天授二年一月至四月西州都督府在安昌、南平兩城開展調查,被調查者除原告唐建進和被告高元禎外,還有合城老人、城主、渠長、知田人、知水人等人員。因文書殘缺,無從得知后續進展,陳國燦先生也只能推斷高元禎是以職田名義侵占逃死、戶絕、還公地,并認為這是反映武周時均田制出現弊端的典型案例。
高元禎案卷相關文書,除陳國燦先生揭示的22件外,還有3件殘片,刊布于朱雷先生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一書。3件殘片皆無墓葬信息、(略),朱雷先生據紙質、內容、格式、筆跡等要素判斷這組文書可以拼合,并指出這組文書與高元禎案卷的關聯,進而將之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謹移文書圖版(圖1)并朱先生錄文如下(本文武周新字皆改為通行漢字,“[殘片A/B/C]”系筆者所加)。[5]
圖1《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所刊《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圖版
從文書樣式判斷,3件殘片皆是辯文。“辯”在唐代是種文體,用于回答官府訊問,節引黃正建先生總結的“辯式”如下。
[1](辯者)姓名、年齡、畫押(指印);[2]訴訟標的(此項不必須有);[3]某(辯者)辯:被問(下列被問事項);[4]仰答者;[5]謹審:(下列回答的內容,往往以“但”字開頭);[6]被問依實謹辯(后面往往有負責處理案卷官員的署名);[7]年月日。[6]
在前述高元禎案卷的22件文書中,至少有10件辯文,樣式大體分為兩類。一類符合黃正建先生總結的“辯式”,如西州都督府勘問李申相、康進感、郭文智等人的辯文。[7]
另一類以西州都督府勘問高元禎的辯文為例:[8]
文書第4行“亦不回換粟麥”之前的內容對應“辯式”第[5]項;之后第4、5行的內容依次對應第[6][7]項。第4行的“感”應是西州都督府“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9]第5行署名是“(略)主簿高元禎”,知文書是西州都督府倉曹勘問被告高元禎的辯文。這件文書與前一類樣式稍異,主要表現在第[6][7]項的“被問依實謹辯”“(某)辯”為“被問依實謹牒”“(某)牒”取代。[10]
《唐六典》云“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11]可能因為辯者身份不同,辯有“辭辯”“牒辯”兩類樣式。就高元禎案卷而言:辭辯的使用者是庶人,而李申相、康進感、郭文智等人的身份是知水人、知田人,則雜任層、雜職層或也使用辭辯;[12]牒辯的使用者應具有官人身份,如主簿高元禎。另參考阿斯塔那239號墓所出《唐景龍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龍四年(710)正月西州(略)墓所出《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謙、薛光泚、康大之請給過所案卷》第1~10行[73TAM509:8/4-1(a)]2件保存相對完整的牒辯,[13]可對唐代“辯式”補充如下。
對照“辭辯”“牒辯”樣式可知,《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收錄的[殘片A]與[殘片B][殘片C]應不是同一件文書。
首先,[殘片A]是原告唐建進的辯文。原22件殘片中也有一件文書被整理者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14]據首行“□□辯被問建進若告主簿營種還公”知,文書確為辭辯。只不過首尾皆殘,可以判定辯者身份的第[1][3][7]項信息皆不完整,所以,文書中雖有“建進”,但無法認定唐建進就是辯者。
而[殘片A]第1行對應“辯式”第[1]項,系辯者的姓名、年齡與指印,知本件辯者確為唐建進。第2行對應“辯式”第[3]項,應是唐建進被問之事項(參考高元禎案卷其他辯文,辯者信息與被問事項間皆無“訴訟標的”一項)。本行以“建進”開頭,可以再次印證辯者身份,只不過“(主)簿于安昌所種田是”前殘缺“被問”二字。據前引高元禎牒辯,唐建進所告應有兩項:一是營種“逃死、□(絕)戶田”,二是“回換粟麥”。另據他人證詞,所涉地域包括(略)轄下的安昌、南平二城。[15]西州都督府倉曹受理高元禎案,需執行“三審”“受辭”等程序,[16]這很可能是本件辯文的生成背景,換言之,相較案卷其他殘片,本件文書的時間可能更早。只可惜文書殘缺,缺少判定文書為辭辯或牒辯的關鍵證據,暫時還不能武斷地認為[殘片A]是辭辯。
其次,[殘片B][殘片C]樣式為牒辯。第3行“牒被問得建進”對應“牒辯式”第[3]項,屬辯者被問事項。第7行對應“牒辯式”第[6]項,是辯文的結句。
值得注意的是,[殘片A]與[殘片B]均包含辯者被問事項,格式重復,是二者分屬不同辯文的力證。
并且[殘片B]“得建進”,不似勘問唐建進的語句。阿斯塔那239號墓所出《唐景龍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龍四年(710)正月西州(略)處分田畝案卷》第64~65行:“牒辯被問得堂兄妻阿白辭稱云籍下田地訴有□得者。縣判準狀問者。”[17]辯者嚴住君之堂兄妻阿白向(略)呈辭,縣司則就此事勘問住君。與前者相似,“得建進”是指辯者接收來自唐建進的文書,故辯者不應是唐建進。加之二者字跡略有差異(尤以“種”字較明顯),[殘片A]與[殘片B]應不是同一件辯文。
而據“牒辯式”,[殘片B][殘片C]格式互補,存在屬同件文書的可能,其辯者可能有一定官職。據第6行的“今款連署”知,辯者可能不只一人。又第4、5行的“種地多納子”“催地子(第5行的‘’似為‘催埊’,之后筆劃或‘子’字)”等信息,說明這件牒辯可能涉及催征高元禎職田地子事。綜合以上信息[殘片B][殘片C]的辯者可能是西州都督府或(略)的官吏。
綜上,《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中原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的一組文書,無法拼合,[殘片A]與[殘片B][殘片C]至少分屬兩件辯文。[殘片A]是勘問唐建進的辯文,但不明辭辯還是牒辯,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殘片B][殘片C]均符合牒辯樣式,暫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
二
在唐建進向州府告發高元禎侵占逃死、戶絕田后,事態發生變化。唐建進突然失蹤,西州都督府遂要求(略)領送唐建進的妻兒、鄰保赴州勘問。記敘該事件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72TAM230:73(a),71(a);以下簡稱《妻兒鄰保牒》]是高元禎案卷的核心文書之一,但學界以往認識存在問題,謹移錄文如下。[18]
從定名判斷,整理者認為文書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知水人康進感等人所上牒文的尾部與西州倉曹下(略)的牒文,但上述判定存在問題。
整理者據“牒”“謹牒”等語詞,判斷第1~2行的殘文書是一件牒文。但唐代文書存在牒、狀語混用現象,以“牒,件狀如前,謹牒”結句者,已被學者考證為唐地方官府所用之狀文。[19]第3~8行是西州都督府處理上件狀文的文案:[20]第3~4行是長官“傑”的署名環節,“傑”即時任都督的王孝傑;[21]第5~6行是受付環節,本應由錄事與錄事參軍事分別執行受、付程序,但此時錄事出使,錄事參軍事亦不在任上,所以由博士“仁”檢校錄事參軍事;第7行并第8行的“十二日”是行判環節,“感”即“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總之,《妻兒鄰保牒》第1~7行(含第8行的“十二日”)分為兩段:第1~2行是康進感等人上西州都督府的狀尾,第3~7行(含第8行的“十二日”)是西州都督府處理狀文的文案,該案由倉曹具體負責。
第8~16行的文書,整理者認為是西州都督府倉曹下(略)的牒文。
首先,發件單位:(略)
其次,其性質是狀文而非牒文。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唐代牒文,除有與敦煌出土P.2819號《唐開元公式令》殘卷之“牒式”(牒式A)相似外,還有與《司馬氏書儀》所收元豐牒式(牒式B)相似者。《妻兒鄰保牒》第8行的“倉曹”是發件單位:(略)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符合第8~16行樣式的文書有3類。第一是帖文,[22]但帖文是一種下行文書,與《妻兒鄰保牒》文書上行的情形不符。
第二是以“牒,件檢如前,謹牒”“牒,件勘如前,謹牒”結句的文案,以斯坦因所獲《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Ast.Ⅲ.4.094)第29~42行為例:[24]
案卷第31~42行系神龍元年(705)三月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長行馬死馬案卷的一部分。案卷涉及兩起死馬事:先是一疋長行馬回至柳谷鎮南五里病死,柳谷鎮狀上州,兵曹判“皮雖檢到,肉價不來,牒所由征還”,此為案卷第4~19行反映的內容;[25]再是兩疋往使伊州的長行馬,醫療不損致死,由長行坊狀上州,都督鄧溫[26]判“檢何故”,此為案卷第20~30行反映的內容。[27]
兵曹遵照都督判,核檢上述兩疋往使伊州之長行馬的死因,確定“無他故”后,制作了第31~41行的文書。末尾除兵曹參軍、府等兵曹官吏署名外,主帥、槽頭、獸醫等長行坊相關責任人也要連署。[28]書訖上行都督處分,鄧溫判“付司”,文書交還兵曹,兵曹參軍程待判“帖槽出賣訖具上”。
總之,綜合吐魯番出土的其他相似文書判斷,第31~41行兵曹這件上行文書,本質仍屬西州都督府內部文案。這類文案的樣式與處理程式并不固定,卻都要審案官員判以“檢”,[29]“件勘如前”亦同理。但第7行的判詞是“連”,亦不符。
第三是狀文。赤木崇敏遍考敦煌吐魯番文書,檢出5件都督府(州、郡)內部由諸曹發出的上行文書,[30]發現唐令雖規定官府內部的上行文書(別局上于本局)使用刺文,[31]但這5件文書無一例外皆是狀文。[32]所以,《妻兒鄰保牒》第8~16行不僅契合狀文樣式,也與西州都督府內部諸曹上行文書的用例相符。
綜上,《妻兒鄰保牒》第8~16行應是一件西州都督府內部倉曹發出的狀文(以下簡稱“倉曹狀”)。
三
“倉曹狀”正文殘有三句:首句是倉曹“準都督判”,同時向(略)(略)令陽愻[33]發文,要求“差人領送”唐建進赴州;次句是倉曹收到“縣申”(當是解文)和縣令“通狀”,答復“追訪建進不獲”,倉曹(略)令“依前捉送”,但始終未有結果;末句是都督再次下令,要求“追建進妻兒及建進鄰保赴州”,并繼續“依前捉建進”。
同墓另有《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72TAM230:58/1(a)~58/4(a);以下簡稱“牒尾判”]與“倉曹狀”內容關聯緊密。[34]
“牒尾判”第1~7行保存相對完整:府司認為唐建進不會逃亡,并要求領送唐建進家口赴州,所述內容大體同于“倉曹狀”,但補充了一些細節。第8~9行雖殘,仍可憑所余筆畫稍作推斷。
第8行前3字似為“二年壹”(“年”字為武周新字,“壹”字大寫),“月”字后或為“起”字。第9行為詞尾,第3字殘有“讠”旁,或為“諮”字;[35]第4字所殘筆畫似為“義”字左下部分,第5字應為“白”字之左上部分。第9行末2字整理者釋讀為“二日”,但“二”字之上似仍有一橫,或為“十”字。總之,可對“牒尾判”第8~9行重新釋文如下:
在唐代文書處理程式中,判官判詞書寫的一般格式是“云云。諮。某白。某日”。[36]從“牒尾判”第9行的格式,并筆跡、內容判斷,“牒尾判”系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判詞(細審圖版,第4字“義”、第5字“白”之間尚余1字空間,或可依理推補康義感之“感”字)。
既然“牒尾判”“倉曹狀”內容高度相關,二者是何關系?回答此問題前應注意可與“牒尾判”綴合的另一件文書——《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72TAM230:72)。先移錄文如下:[37]
從簽署官吏“史孫行感”“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知,這件僅余尾部的文書,也由西州都督府倉曹發出(以下簡稱“倉曹文尾”)。并且有2點可證“倉曹文尾”能與“牒尾判”綴合。
第一,兩件殘片茬口耦合,從縫背無押署判斷,兩殘片系同一張紙。
第二,從“倉曹文尾”到“牒尾判”,是連貫的處理程式。“倉曹文尾”第3~7行是西州都督府的署名、受付環節,之后應是判案環節,此環節一般先由判官行判。據第7行的“付倉”可知,文書交還倉曹處理。而“牒尾判”剛好是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判詞,且“牒尾判”末行的“十二日”也與“倉曹文尾”署名、受付日期一致。
總之,“倉曹文尾”有較大概率可與“牒尾判”綴合。
明確“倉曹文尾”與“牒尾判”的關系,可進一步推知“倉曹狀”與“倉曹文尾”可能是同件文書。換言之,“倉曹狀”“倉曹文尾”“牒尾判”3件殘片可以拼合。
第一,“倉曹狀”與“倉曹文尾”闊度相近,書法筆跡一致,皆應出自倉曹史孫行感之手。
第二,從文尾署名與西州都督府的處理環節判斷,“倉曹文尾”也是西州都督府內部由倉曹發出的上行文書,這與“倉曹狀”情況相同。
第三,既然“倉曹文尾”與“牒尾判”可以綴合,則“牒尾判”應是“倉曹文尾”的判文。而“倉曹狀”又與“牒尾判”內容高度相關,說明“倉曹狀”“倉曹文尾”的內容很可能也有關聯。
第四,3件殘片的時間也可提供線索。復引《妻兒鄰保牒》第7~8行如下:
康義感在判“連,感白”后,將“十二日”簽在后件“倉曹狀”上(第8行),表明康義感很可能在行判前件“康進感狀”時,就已收到了完成付司、受付的“倉曹狀”。所以,“倉曹狀”付司、受付日期應不晚于十二日,行判日期也應與十二日相近。而“倉曹文尾”的付司、受付日期,“牒尾判”行判日期剛好同為十二日。
拼合后的文書也符合連貫的處理程式。第7行“連”的判白正是對“倉曹狀”的預處理。“連”作為吐魯番文書的常見判詞,是判官在判案前要求主典將同類文書粘連,留待一并處理的措施。“連”與“檢案”是相反的一組判詞,“連”一般要求主典粘連兩件未了結的文書,而“檢案”則要求主典將新到文書與此前了結的文案粘連。文書處理一般要經過署名、受付、判案、執行、勾稽、抄目6個環節,[38]完成抄目后的文案可視作了結的狀態。以大谷文書5839號《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為例(“[第4/5紙]”系筆者據《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所加)。[39]
大谷文書5839號由相連的6紙組成,[第1紙][第6紙]殘缺不全,[第2~5紙]保存完整。據抄目推測,[第1紙]應是西州都督府兵曹、法曹的請紙文書,殘有都督署名,錄事與錄事參軍受付的文案。這件請紙文書依次經過判官、通判官、長官的判署程序([第2紙]),及執行、勾稽、抄目的程序([第3紙]),到[第3紙]22行為止,兵曹、法曹請紙案已了。[第4紙]是件新文書,由(略)完整地呈現了官司向州府請紙的行政運作過程,[40]從中可以看出,“檢案”與“檢案連如前”相對應,是將新到文書與此前已了結的文案粘連。
“連”則要求主典粘連兩件未了結的文書。仍以斯坦因所獲《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圖2)為例。[41]
圖2Ast.Ⅲ.4.094《唐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案卷》(局部)[42]
關于神龍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處分死馬事的行政運作過程,前文已有論述。上述引文由3部分構成:第1~3行是收件單位:(略)
總之,“連”與“檢案”均要求主典粘連文案,區別在于:“檢案”是將新到文書與已了結的文案粘接,主典署“檢案連如前”;“連”粘連的都是沒有經過完整處理程式的文書,主典無需署名。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判官在騎縫線附近署“連”的情況屬于特例。但正是因為經歷了“連”這一預處理的程序,判錄事參軍康義感得以在“倉曹文尾”后直接行判,即“牒尾判”反映的內容。
同樣經過預處理后直接行判的狀文,還有阿斯塔那188號墓所出《唐神龍二年(706)主帥渾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狀為處分馬料事》[72TAM188:82(a)]:[43]
對照前引狀式,從“狀上”“謹以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判斷,第5~11行的文書是唐神龍二年二月某營上西州都督府的狀文。狀文到達西州后,依次經過署名、受付、判案等環節,第16、17行的判詞雖簡短,從“某諮某白”的格式判斷,也與“倉曹文尾”“牒尾判”的情況相似,屬判官即刻行判的例證。之所以能即刻行判,是因為渾小弟狀在到達西州后先經過了預處理,即第1~4行的內容。第1行的“事”即第5~11行的渾小弟狀,主典在渾小弟狀前接一紙,寫明狀文到來這一情況,署名后交由判官行判,敬仁判“連”,即將渾小弟狀同其他文書作并案處理。完成這些預處理后,遂有第16、17行的判白。
總之,上文通過繁復考證旨在說明,從“倉曹狀”到“牒尾判”是連貫的處理程式,既符合唐代的行政運作原則,也能在其他吐魯番文書中找到相似例證。
綜合上述五點,“倉曹狀”與“倉曹文尾”有極大可能是同件狀文,而“牒尾判”就是倉曹在處理這件狀文時的判詞,拼合后的文書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圖3)。進而可復原行政運作流程如下:武周天授二年一月十一日,知水人康進感等人向西州都督府呈交了一件狀文,接到狀文后都督王孝傑與錄事司博士攝(檢)錄事參軍“仁”即日作出處理;大約在此前后,倉曹呈交了另一件狀文,內容是向都督匯報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相關事宜,狀文在十二日完成付司與受付的流程;倉曹在同一時間處理了這兩件文書,在完成粘連工作后,判倉曹參軍康義感于兩件文書粘接處判“連”并署上姓名、日期,并在狀末——“博士攝錄事參軍付倉”的后一行書寫判詞,判詞寫至“仰準長官處分,即”,一紙用盡,又續一紙。
圖3《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拼合圖
結論
唐代逃亡問題武后統治時開始嚴重,[44]浮逃戶等問題導致逃死、戶絕田大量出現,給予地方官僚侵占之機,這便是高元禎案產生的背景。這一時期,全國曾開展勘查田土、檢括戶籍的活動,[45]以應對百姓大量流移的社會情勢。所以,在天授初年革唐建周的“敏感時期”,發生侵占逃死、戶絕田的“敏感案件”,高元禎案不僅備受西州官府的重視,或許也會牽動更高層統治者的神經。從殘存的高元禎案卷看,本案持續時間較長、涉及人物眾多、情節發展曲折,所以相關文書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是探討唐代田制與地方行政制度的珍貴史料。
同時,這也增加了整理難度,尤其考慮到案卷“殘缺已甚”“不能銜接”的現狀。[46]而《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新收錄一組案卷殘片,朱雷先生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1~3),對重新整理高元禎案卷有重要意義。在案卷原有的22件殘片中,也有1件文書被整理者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辭》(72TAM230:67),但因判斷辯者身份的核心信息缺失,暫無法據“辯式”論定辯者為唐建進。收錄于《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的這組文書,3件殘片均為辯文:第1件殘片據“辯式”可確知,辯者為唐建進;但第1件殘片與第2、3件殘片存在格式重復的情況,應至少分屬兩件辯文;第2、3件殘片格式互補,存在同屬一件辯文的可能,辯者可能是西州都督府或(略)的官吏,性質為牒辯。因此3件殘片無法拼合,宜分別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據唐代官司受理“告言人罪”的規定,西州都督府受理高元禎案,需對原告唐建進執行“三審”“受辭”等程序,所以倉曹勘問唐建進的辯文或可視作高元禎案卷的開端。
但隨著原告唐建進的隱匿,案情迎來重要轉折,記錄該事件的《武周天授二年(691)知水人康進感等牒尾及西州倉曹下(略)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牒》[72TAM230:73(a),71(a)]也是案卷核心文書之一。這件文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知水人康進感的狀文,二是西州都督府內部倉曹的上行文書。后者其實與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72TAM230:72)是同一件狀文,他們又能與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追送唐建進家口等牒尾判》[72TAM230:58/1(a)~58/4(a)]綴合,拼合后的文書宜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本案中被告高元禎乃(略)主簿,系從九品上官。[47]據《唐律疏議》“輒自決斷”條疏議引《獄官令》,“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斷徒及官人罪”,[48]又按明鈔本《天圣令》宋2條,“若官人犯罪,具案錄奏,下大理寺檢斷”,[49]因為官人犯罪的性質,高元禎案當交由大理寺等機構審理,但前期調查工作由西州都督府及(略)承擔。本件文書作為“具案錄奏”的重要依憑,反映了西州都督府行政運作的生動細節。
最后附新錄文于后,通過案卷文書的再整理,希望能對學界正確利用這批材料提供一些參考。
《武周天授二年(691)唐建進辯》(72TAM230:67/1)
《武周天授二年(691)某人牒辯》(72TAM230:67/2,3)
《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倉曹案卷為追送唐建進妻兒鄰保事》[72TAM230:71(a)~73(a),58/1(a)~58/4(a)]
滑動查閱注釋
[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略):17ZDA183)的階段性成果。
[2]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0頁。
[3]李征、沙知、宋家鈺、陳國燦、楊際平、小田義久、李文瀾、趙呂甫、李方等先生曾對案卷文書有過討論,相關研究可參見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略),2002年,第133頁。此外還有齊陳駿:《簡述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職田的資料》,《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40~49頁;寧可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150~161頁;盧向前:《唐代西州土地關系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4~296頁;王曉暉:《西州水利利益圈與西州社會》,《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52~60頁;劉子凡:《唐前期西州(略)水利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第52~63頁;雷聞:《隋唐的鄉官與老人——從大谷文書4026〈唐西州老人、鄉官名簿〉說起》,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1~156頁;楊際平:《論唐、五代所見的“一田二主”與永佃權》,《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7頁;呂冠軍:《吐魯番文書中的“雙名單稱”問題》,《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第80~87頁;裴成國:《唐西州契約的基礎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42~58頁;趙曉芳,郭振:《唐前期西州鄰保組織與基層社會研究——(略)》,《敦煌學輯刊》2020年第2期,第91~107頁;魯西奇:《父老:中國古代鄉村的“長老”及其權力》,《北京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89~101頁等。
[4]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455~485頁;后收入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1~392頁。
[5]參見朱雷:《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巴蜀書社,2022年,第83頁。
[6]黃正建:《唐代法律用語中的“款”和“辯”——以〈天圣令〉(略)》,《文史》2013年第1輯,第261頁。
[7]西州都督府勘問李申相的辯文有2件殘片,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西州都督府勘問康進感的辯文有1件殘片,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4頁。西州都督府勘問郭文智的辯文有3件殘片,包含2件辯文,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墓之文書,也符合這種樣式。前者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6頁;后者錄文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43、144頁。
[8]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79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四卷,法藏館,2010年,図版八一。
[9]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91)史孫行感殘牒》有“參軍判倉曹參軍康義感”的署名(詳后)。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
[10]大谷文書4908號勘問康才智的辯文也是這種樣式,錄文參見陳國燦:《對西州都督府勘檢(略)主簿高元禎職田案卷的考察》,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80、381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図版八。
[11]〔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條,中華書局,1992年,第11頁。
[12]渡邊信一郎認為外職掌中,除了流外官,雜任層和雜職層都由色役來征發,仍屬于百姓。這可能是雜任層、雜職層也使用辭辯的原因。參見〔日〕渡邊信一郎著;吳明浩,吳承翰譯:《中國古代的財政與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488頁。
[13]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叁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59頁;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268頁。
[14]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2頁。
[15]參見陳國燦:《唐西州的四(略)制》,劉安志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新探(第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29頁。
[16]明鈔本《天圣獄官令》宋29條載官司受理“告言人罪”的規定,雷聞先生據《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通典》卷一六五《刑法·刑制》等材料,參考宋29條,復原為《開元獄官令》第35條:“諸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并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略),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于審后判記,審訖,然后付司。……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參見雷聞:《唐開元獄官令復原研究》,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第623、624頁。
[17]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叁卷,第559頁。
[18]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0頁。
[19]中村裕一、赤木崇敏、吳麗娛、黃正建、包曉悅等學者都曾討論過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牒、狀語混用現象,目前仍有爭論。筆者認為,這類文書在唐前期能否稱為狀文,需要進一步討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類文書在唐前期已具有比較穩定的文書樣式和應用范圍。為方便行文,依赤木崇敏的歸納,暫稱為“狀文”。參見〔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9頁。
[20]關于唐代文書的處理程式,可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9~363頁。
[21]參見李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11頁。
[22]關于唐代的帖式,可參見雷聞:《唐代帖文的形態與運作》,氏著:《官文書與唐代政務運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89~91頁。
[23]〔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第126、127、129頁。
[24]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52、253頁。
[25]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49~251頁。
[26]參見李方:《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第12、13頁。
[27]參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51、252頁。
[28]荒川正晴注意到長行坊發出的許多牒、狀有主帥與押官的聯名簽署,并認為主帥、押官等鎮守指揮官實質上干預了長行坊的運營和管理。參見〔日〕荒川正晴著;馮培紅,王蕾譯:《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25頁。
[29]參見劉安志:《關于吐魯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2018年第3期,第96頁。
[30]以年代為序,4件文書的發出單位:(略)
[31]參見〔日〕吉川真司:《奈良時代の宣》,氏著:《律令官僚制の研究》,塙書房,1998年,第216~218頁。
[32]參見〔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體制——(略)》,鄧小南,曹家齊,〔日〕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第143~145頁。
[33]細審圖版,原錄文之“懸”字應為“愻”字。
[34]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1頁。
[35]敦煌吐魯番唐代文書中“諮”字之“言”旁多已簡化為“讠”旁。參見劉安志:《關于吐魯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2018年第3期,第101頁。
[36]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第349頁。
[37]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3頁。
[38]參見盧向前:《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唐公式文研究》,氏著:《唐代政治經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第329~363頁。
[39]錄文據榮新江,史睿主編:《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中華書局,2021年,第470~474頁;圖版參見〔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図版九。關于《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所見西州行政運作的研究,可另參見雷聞:《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唐代公文用紙》,氏著:《官文書與唐代政務運行研究》,第222~247頁。
[40]還可參見《唐開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請紙案卷》的其他殘片,如黃文弼文書H31號((略)據《黃文弼所獲西域文書》)、大谷文書5840號等。錄文并參見榮新江,史睿主編:《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第474~481頁。
[41]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第248~252頁。
[42]圖片源自“國際敦煌項目”(IDP)官網,訪問鏈接:https://(略).D475D401B881/?return=%2Fcollection%2F%3Fterm%3D4.094,訪問日期:2024年5月12日。
[43]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26頁。(略)的研究,可參見孫繼民:《從渾小弟一組文書看唐代早期健兒制度的幾個問題》,氏著:《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6~80頁。
[44]唐長孺:《唐代的客戶》,氏著:《山居存稿》,中華書局,2011年,第135頁。
[45]參見陳國燦:《吐魯番舊出武周勘檢田籍簿考釋》,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12~328頁;陳國燦:《武周時期的勘田檢籍活動——對吐魯番所出兩組敦煌經濟文書的探討》,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第329~370頁。
[46]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肆卷,第70頁。
[47]唐代(略)(略),下縣主簿為從九品上官。參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三〇“京(略)天(略)官吏”條,第752頁;《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7頁。
[48]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卷三〇《斷獄·輒自決斷》,中華書局,1996年,第2065頁。
[49]校錄本《天圣令》卷二七《獄官令》,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第327頁。
(作者單位:(略)
編校:宋俐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霞
掃碼關注我們微信:(略)
郵箱:(略)
|
關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上文為隱藏信息僅對會員開放,請您登錄會員賬號后查看,
如果您還不是會員,請點擊免費注冊會員
|
||||||||||
最新招標采購信息
更多吐魯番招標采購信息
熱點推薦
熱門招標
熱門關注
- 塔城招標網
- 哈密招標網
- 和田招標網
- 阿勒泰招標網
- 克孜勒蘇招標網
- 博爾塔拉招標網
- 克拉瑪依招標網
- 烏魯木齊招標網
- 石河子招標網
- 昌吉招標網
- 吐魯番招標網
- 巴音郭楞招標網
- 阿克蘇招標網
- 喀什招標網
- 伊犁招標網
- 阿拉爾招標網
- 圖木舒克招標網
- 五家渠招標網
- 北屯招標網
- 鐵門關招標網
- 雙河招標網
- 可克達拉招標網
- 昆玉招標網
- 隆化縣農業農村局
- 合肥大學
- 邵陽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 貴州盤江電投發電有限公司
- 葉城縣夏合甫鄉小學
- 南沙區人民政府
- 馬鞍山教育局
- 廣州市電化教育館
- 湖南省體操運動管理中心
- 常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武進分中心
- 重慶南桐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 南通市城鎮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西安高壓電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 婺源縣自然資源局
- 國能山東置業有限公司
- 廣西|壯族自治區藥械集中采購網
- 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隊
- 桂陽縣政務服務中心
- 云南紅塔藍鷹紙業有限公司
- 北京郵電大學世紀學院
- 洛浦縣阿其克鄉衛生院
- 江西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
- 榆樹市水利局
- 隆化縣財政局
- 烏魯木齊市烈士陵園
- 成都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廣東省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
- 航天萬源實業有限公司
-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保健中心
- 青島市黃島區交通運輸局
- 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金隅臺泥(代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 江蘇怡寧能源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東莞市應急管理局
- 中冶沈勘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 沈陽市蘇家屯區房產局
- 蘇州太湖新城吳中管理委員會
- 寧夏政府|采購網招標公告
- 安徽省工程建設招標采購網
- 四川省鐵路建設有限公司
- 長沙市政府采招標公告
- 南京市招投標協會
- 龍城區應急管理局
- 合肥百姓網
- 龍巖醫療器械采購平臺
- 堡壘機招標
- 高青縣政務服務中心
- 一汽電子招標
- 吉林省政府采購招標平臺
- 山東財經大學
- 福建工程學院管理學院
- 全球采購中心
- 漳州市政務服務中心
- 煙臺開發區招標公告網
- 安徽采購國產醫療器械
- 樊城區人民政府
- 承德市平泉市
- 延邊州人民政府
- 招標|資源網下載
- 蘭陵縣教育局
- 縉云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上海復星長征醫學科學有限公司
- 漯河公共資源交易網
- 岳陽縣人民政府
- 北京裝飾裝修招標信息
- 召陵區政務服務中心
- 安吉縣政府采購中心
- 濟南招標公司
- 香河縣|招投標中心
- 陽光招標網
- 諸暨招標網
- 山東高速集團|有限公司招標信息
- 合川市建設信息港
- 宿城區人民政府
- 陵川縣|招投標中心
- 建設資源交易中心
- 安陽縣教育局
- 安化縣人民政府
- 金壇經濟開發區
- 遼寧省招標投標管理辦法